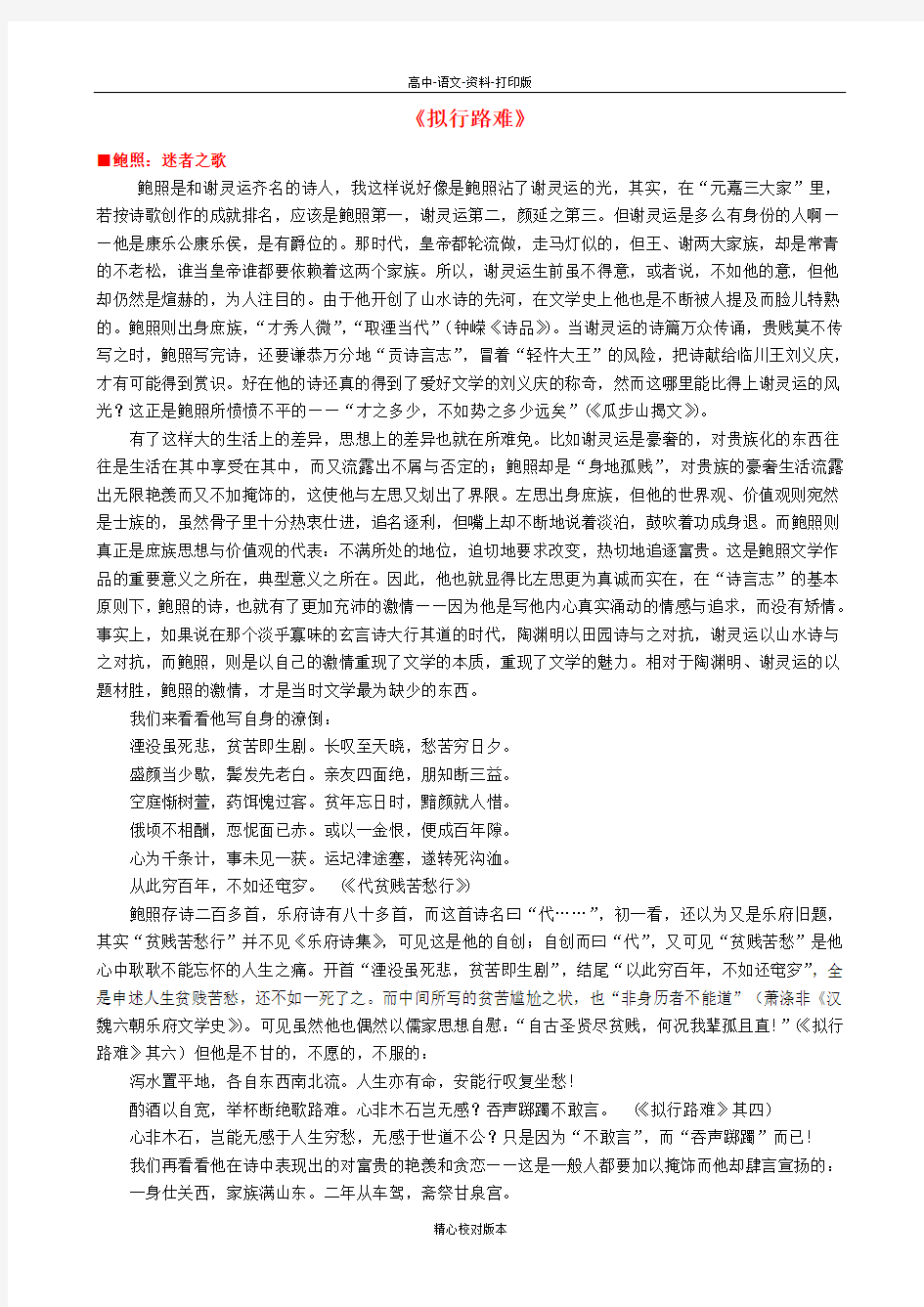

《拟行路难》
■鲍照:迷者之歌
鲍照是和谢灵运齐名的诗人,我这样说好像是鲍照沾了谢灵运的光,其实,在“元嘉三大家”里,若按诗歌创作的成就排名,应该是鲍照第一,谢灵运第二,颜延之第三。但谢灵运是多么有身份的人啊——他是康乐公康乐侯,是有爵位的。那时代,皇帝都轮流做,走马灯似的,但王、谢两大家族,却是常青的不老松,谁当皇帝谁都要依赖着这两个家族。所以,谢灵运生前虽不得意,或者说,不如他的意,但他却仍然是煊赫的,为人注目的。由于他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在文学史上他也是不断被人提及而脸儿特熟的。鲍照则出身庶族,“才秀人微”,“取湮当代”(钟嵘《诗品》)。当谢灵运的诗篇万众传诵,贵贱莫不传写之时,鲍照写完诗,还要谦恭万分地“贡诗言志”,冒着“轻忤大王”的风险,把诗献给临川王刘义庆,才有可能得到赏识。好在他的诗还真的得到了爱好文学的刘义庆的称奇,然而这哪里能比得上谢灵运的风光?这正是鲍照所愤愤不平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
有了这样大的生活上的差异,思想上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比如谢灵运是豪奢的,对贵族化的东西往往是生活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而又流露出不屑与否定的;鲍照却是“身地孤贱”,对贵族的豪奢生活流露出无限艳羡而又不加掩饰的,这使他与左思又划出了界限。左思出身庶族,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则宛然是士族的,虽然骨子里十分热衷仕进,追名逐利,但嘴上却不断地说着淡泊,鼓吹着功成身退。而鲍照则真正是庶族思想与价值观的代表:不满所处的地位,迫切地要求改变,热切地追逐富贵。这是鲍照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典型意义之所在。因此,他也就显得比左思更为真诚而实在,在“诗言志”的基本原则下,鲍照的诗,也就有了更加充沛的激情——因为他是写他内心真实涌动的情感与追求,而没有矫情。事实上,如果说在那个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大行其道的时代,陶渊明以田园诗与之对抗,谢灵运以山水诗与之对抗,而鲍照,则是以自己的激情重现了文学的本质,重现了文学的魅力。相对于陶渊明、谢灵运的以题材胜,鲍照的激情,才是当时文学最为缺少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他写自身的潦倒:
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
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
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
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
从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代贫贱苦愁行》)
鲍照存诗二百多首,乐府诗有八十多首,而这首诗名曰“代……”,初一看,还以为又是乐府旧题,其实“贫贱苦愁行”并不见《乐府诗集》,可见这是他的自创;自创而曰“代”,又可见“贫贱苦愁”是他心中耿耿不能忘怀的人生之痛。开首“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结尾“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全是申述人生贫贱苦愁,还不如一死了之。而中间所写的贫苦尴尬之状,也“非身历者不能道”(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可见虽然他也偶然以儒家思想自慰:“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其六)但他是不甘的,不愿的,不服的: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拟行路难》其四)
心非木石,岂能无感于人生穷愁,无感于世道不公?只是因为“不敢言”,而“吞声踯躅”而已!
我们再看看他在诗中表现出的对富贵的艳羡和贪恋——这是一般人都要加以掩饰而他却肆言宣扬的: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
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
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座,组帐扬春风。
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
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数名诗》)
除了最后两句有些愤怨(其实也夹杂着更多的艳羡)外,那种对车骑、宴饮、歌舞等物质享受充满叹慕的描写,对“家族满山东”、“休沐还旧邦”、“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的成就感及虚荣心的满足等,都全不似传统士人的口吻,这是典型的市井下层人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眼光与趣味——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趣味与追求,而是他们都掩饰了这种趣味。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上,人们是贬低这些的。所以,人们总是掩饰自己的这种追求。左思说的“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这才是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肯定与赞赏的,也是对人们的要求——一方面要立功,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另一方面又要拒绝个人富贵,免得这种个人的利益追求玷污了“公益”的追求。
可是鲍照的趣味就是下层的,因而是活泼的、真实的,我们看他的《白纻歌六首》其二:
桂宫柏寝拟天居,朱爵文窗韬绮疏。象床瑶席镇犀渠,雕屏铪匝组帷舒。
秦筝赵瑟挟笙竽,垂珰散佩盈玉除,停觞不语欲谁须。
你看他笔下的事物,哪一样不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诗品》说他的诗歌“险俗”,固是确评。他就是俗,他的世界观、他的审美观、他的趣味都是“俗”,而且那么理直气壮,俊逸、壮丽、豪放,“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他就热爱这些俗艳的东西,富贵的东西,感性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我们再看他的这一首《拟行路难》其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写人生的华丽与心底的悲凉。他铺排华丽之时,早已心如死灰,但他心如死灰之时,仍旧铺排华丽!这就是生命力!
就题材言,鲍照不仅写出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而且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和宫体诗,他的边塞诗是中国边塞诗史上重要的一环,是唐朝之前边塞诗最值得珍视的作品。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诗,写女性的情与态,大胆而又露骨——他笔下的女子,也是富于激情的。他的这些艳情诗,又是梁陈宫体诗的先声。一个热衷于江山塞漠的人也醉心于宫廷闺闱,这似乎不大和谐,其实却十分合乎逻辑:因为无论边塞还是闺闱,都是最能激发生命冲动的地点;无论敌人还是美人,又都是最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对象。鲍照是一个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人,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需要杀戮与征服,需要死亡与爱恋——马背与女人的玉胸,是他的天堂,而死亡与生殖,最能搅动他的热血。
我们选一首他的艳情诗看看,《代淮南王》其二:
朱城九门门九开,愿逐明月入君怀。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
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你看这样的女子,是不是柔情似水更热情似火?
就体裁言,鲍照亦有大贡献,其一,是他的乐府诗创作成就非凡。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五编“南朝乐府”中,为之单列一章,称赞鲍照的乐府诗在南朝犹如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并说以诗言,陶鲍谢三家,后先鼎足,以乐府言,则当让鲍照独步。而萧涤非把鲍照称为“汉乐府大作家”,乃是因为鲍照乐府,其意识体裁,皆与两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为近,而与当时(南朝)荡悦淫志,宣丑之制实
相远。其二,是他在七言诗创作上的贡献。可以说,七言诗到了他这里,不仅被大量使用,而且几近成熟。他可能仅仅想寻找一种新节奏来宣泄他的感情,七言诗这种一挫三折的新节奏较之五言的平稳,更多一种流转与顿宕,而这与他内心充沛的激情是相宜的。所以我们这样说,七言不是他的试验物,而是他心灵的自然反映。所以,对于七言,他几乎是一用便自然,便流畅,便成熟。鲍照之用七言,正如李白之用古风,是外在的形式契合了内在的心灵。对了,说到李白,我有必要点一下,李白的看家本领,即来自于鲍照。
在鲍照的那个时代,陶渊明转向了田园,谢灵运游荡于山水,他们对这个世界,一个是淡泊相忘,一个是厌恶相烦,他们给这个世界的,是背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悟者”,他们看穿了,看厌了,也就心冷了。可是,诗人都远离了去,还有谁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对人的生活保持着那一份关注?此时的鲍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者”,迷恋着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一切,红尘滚滚,情欲深深,而且他在才华上、艺术上又如此毫不逊色。那时代的三支笔,一支写田园,一支写山水,一支写社会;一支写两相忘,一支写两相烦,一支写两相缠。有淡泊的,有厌恶的,他们都想抽身而出,但这边还有一个羡慕的,他却投身而入,他是面向世界的。陶渊明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他写出了世道的凶险与肮脏,为了全身,他退出了。而鲍照则正相反:“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飞蛾赋》)轻死邀得,死而不悔,以身殉利,堂皇不惭。“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行京口至竹里》)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世道虽然黑暗,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雌伏以避,还是有强韧者搏击其中:“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踌伫。”(《代棹歌行》)人生风浪固然险恶,但君子仍然自强不息。鲍照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下层的活力,这是一个社会不死的保障,是生活之河不会停滞的保障。当上层社会对人生厌倦时,下层社会仍然对人生充满渴慕;当上层社会对一切丑陋麻木并从中获益,或对之绝望而“怀宝迷邦”时,下层社会的反抗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看到当陶渊明描写着他的淡泊无争,谢灵运在竭力表达着他的遁世无闷时,鲍照在他的诗歌里表达着他的愤怒。因为他对这个社会还在生气,所以,不仅他的作品虎虎有生气,而且也显得这个社会尚有生气。当“悟者”(陶、谢都自称是“悟者”)抽身而去,弃世界如弃敝屣时,“迷者”如鲍照,就成了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战士。他歌唱的,才是真正的战歌。他可能不够纯洁,但是,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需要纯洁的婴儿,而需要血污斑斑的战士。
■悲歌一曲诉愁肠──鲍照《拟行路难》第四首赏析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这是南朝宋代著名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诗人寄激情于平淡,以浑朴的笔调,表达了沉郁不舒的情怀。
鲍照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寒微的文人往往空怀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不得不在壮志未酬的憾恨中坐视时光流逝。即使跻身仕途,也多是充当幕僚、府掾,备受压抑,在困顿坎坷中徒然挣扎,只落得身心交瘁。鲍照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他出身寒素,“身地孤贱”,无高贵的门第可资凭借。虽然年轻时即以诗为临川王刘义庆所赏识,但始终不得志,一生中只做过诸如王国侍郎、县令、中书舍人、参军等一类小官。尽管他的诗文在南朝时已和谢灵运一样,成为很有影响的三体之一,尤其是他的乐府诗“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一),但是这样一位重要诗人居然史书无传,仅在《宋书》及《南史》的《临川王义庆传》中附带提到几句。由此可见鲍照身前身后寂寞冷清境况之一斑!难怪钟嵘为之叹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仕途的艰难,世道的不平,世人的冷眼,像铅似的乌云笼罩着诗人敏感的心灵,而在精神压抑中迸发出来的愤懑之情,也往往在他的笔端化为警世的闪电,直指黑暗的现实。上面提到的《拟行路难》第四首,即是鲍照此
类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这是人们习见的现象,真实而又平常。诗人拈出这一平常无奇的自然现象作为比兴,以引出他对社会人生的百般感慨,这就使他的感慨也来得那么自然。它发自真实的生活感受,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人的命运就像那“各自东西南北流”的泻地之水一样,漂泊到何处?流逝到何方?是平坦无阻?还是一路颠沛?这都是安排定了的,苦恼也没有用。乍读之下,似乎诗人是在不动感情地叙述一个客观的道理,似乎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人生亦有命”的现实。其实不然。只要深研诗意,就可以体会到诗人故作恬淡的语言中蕴含着多少愤慨!地,岂是平的?泻水置地,难道不是依照各自高下不同的地势而流向各方吗?一个人的遭际如何,犹如泻水于地,不也是被他出身的贵贱、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了吗?纵使你有出众的才华,又如何能越过这“地势”的沟堑,又如何能冲破这门阀的藩篱呢!如果我们结合鲍照的另一篇作品《瓜步山楬文》就更能体会到“泻水置平地”的内在含意。他在楬文中借山川景物来发议论,抨击凭借势利、窃踞高位的烜赫之辈。他指出,瓜步山之所以能“凌清瞰远,擅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诗人在这里,也是借“泻水置平地”这一自然现象来含蓄地抨击“人生亦有命”这一畸形的社会现实。诗人巧妙地运用反嘲的笔法,在质朴平淡的诗句中寄寓了深沉的叹喟。他越是说人生有命是正常的,就越是显出这一现实的荒唐;他越是平静地说“安能行叹复坐愁”,就越是透露出精神上无可解脱的痛苦;他越是自我宽解,故作超脱之语,我们就越是感受到他那颗被压抑的心灵在对命运苦苦地抗争。
“泻水”四句是第一层意思,言不当愁。不当愁,而愁苦偏偏郁结于胸,那么只有借酒浇愁了。于是,诗歌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层:“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对“举杯断绝歌路难”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说“断绝”指歌断绝,“声为君断绝”之意(鲍照《发后渚》);一说“断绝”指断绝愁思,“裁悲且减思”之意(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细味全诗,我觉得后者更为贴切,意境更为完整。《行路难》本是民间歌谣,主旨乃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晋书》记载,袁山松曾作《行路难》,“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其辞以悲愤为主,其调多悲凉之音。“酌酒且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句,以非常精练的笔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诗人悲怆难抑的情态。试想一下,酌酒原为排遣愁怀,然而满怀郁结的悲愁岂是区区杯酒能驱散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平添的几分酒意反倒更激起了愁海的狂澜,诗人趁着酒意击节高歌,唱起了凄怆的《行路难》,将一腔悲愤倾泻出来。长歌当哭,这是何等悲烈景况!读者从这举杯驱愁却大放悲声的情节中,也可以想见其悲其愁的沉郁了。
再往下,诗人没有顺着“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的诗意,继续作解愁之语,而是笔锋一转,掀起新的波澜:“心非木石岂无感。”这是对前面几句的总结。诗人那驱不散的愁苦,实系于对世事的感慨,心并非无知无觉的木石,更何况诗人生就一颗格外敏感的心,怎能不中情激荡、百感俱生呢?“心非木石岂无感”,这一反问句式用得很精采。无论是以理劝喻,还是酌酒自宽,都表明诗人在竭力压抑内心的情感,强说愁叹之情不当有。但是“心非木石岂无感”像一声疾雷震霆,滚滚而来,冲决了自我克制的堤防。它充满了感情力量,就像从诗人备受压抑的心房中突然迸跳出来的。它不是简单地说明一下“人心有感”这一事实,而是以反问的口气在大声疾呼,带着一股强烈的抗争意味。这时,诗的意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诗人的感慨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理的劝喻、酒的麻醉,难道就能使心如槁木吗?当然不能!全诗的情感在这句达到了高潮。紧接着,一个陡然转折,急转直下:“吞声踯躅不敢言。”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情绪由极高至极低,如瀑布跳崖,跌宕起伏,给人以鲜明的对比感。前面的“心非木石岂无感”是那么慷慨义愤,后面的“吞声踯躅不敢言”又是那么无可奈何。“岂无感”越是激昂,“不敢言”的痛苦就越是深沉。这富于戏剧性的对照,将诗人忍辱负重、矛盾痛苦的精神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我们怎能不为诗人不幸的命运而喟然长叹呢?
从艺术上看,鲍照的这首《拟行路难》语言很质朴。全诗用近乎口语的文字写成,明白晓畅。诗人并
非为写诗而造情,而是在倾诉衷肠,一吐为快,诗句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流出来,显得十分真切感人。正因为它并非以文为饰,没有以辞伤意之弊,故全诗气势连贯、浑然一体。这显然得力于汉乐府的影响。不过,语言平易还不足以说明这首诗的特点。更难得的是鲍照用如此浅近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含蓄的诗意和深沉的感情。如“泻水置平地”的比喻很浅近,但如前所分析的,它包含了复杂的现实内容。又如“岂无感”三个字并不深奥,但在鲍照的笔下,它既申诉了愁叹之情的合理性,又蕴含着对精神压抑的抗议。这些并不那么率直的诗意,都要从那质朴的语言中去细细体会。语言的平易与诗意的深邃,二者的融汇,使诗歌古朴而不流于浅露,含蓄而不失于生涩,具有一种浑朴莽苍的格调。
如上所说,此诗不以文辞取胜,而以真情动人。全诗情感变化的层次清晰。开头四句感情比较平静,使人明显感到诗人以理智克制情感的奔泻。到饮酒自宽时,理智的防线在瓦解,情感的流动加快了;终于,《拟行路难》的悲歌冲口而出,情感之流直泻而去。到“心非木石岂无感”句,诗情沸腾,就像卷石冲岸的巨涛一样迎面涌来。最后“吞声”句,好似一道铁闸落下,将奔流的情感陡然截住,造成大起大落的艺术效果。从这完整的感情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想到诗人日常的精神状况:他常常将满腹心事深藏,而强作平静;只有在凭几独斟时,趁着酒兴,慷慨悲歌、愤然陈词。然而,一悟到置身何处,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忍气吞声。鲍照以短短的八句之章,将复杂的心路历程表现得那么曲折婉转,足见诗人驾驭语言的非凡功力。
这首诗在音律上也有独特之处。前四句中,第一句和第三句,第二句与第四句分别押韵,错落有致,不仅读起来抑扬顿挫,而且旋律也显得舒缓平稳。而从“酌酒以自宽”句起,随着潜在情感的变化,骤然换韵,而且由先前的隔句押韵,变为一韵到底,使诗歌的旋律如狂飙直下,因而产生了一种激越、奔放的音乐效果。韵律的变化与情感的进程相协调,这就使情感起伏跳动的效果更加鲜明。
这首诗的立意也很巧妙。它本写一段愁情,却偏偏说“安能行叹复坐愁”,这就越发突出了此愁之难言。他说“心非木石岂无感”,却始终不曾点破所感为何,就更显得此愁之无边无涯。它郁积不散,触处皆是。一读之下,令人不由得与诗人一起扼腕怅恨!
(选自《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