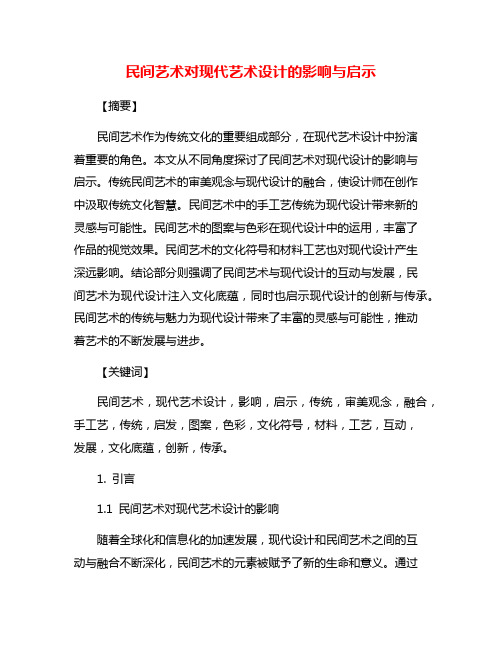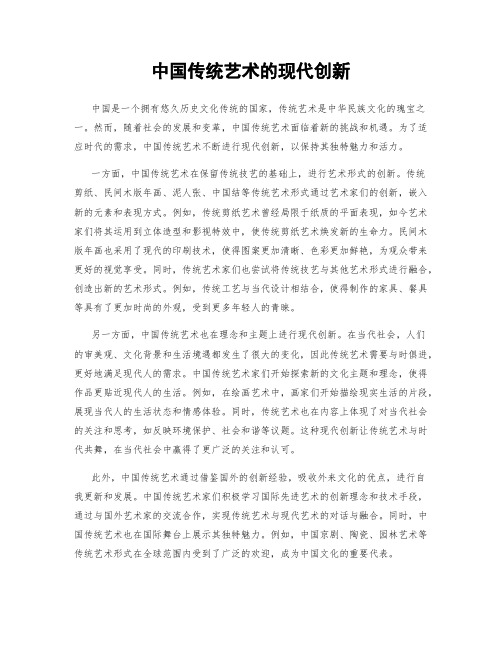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单纯使用工具的技术、技艺状态进入到使研究方法融汇到对象的整体的、富于感情的把握,这也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司各特就谈到二三十年代开始使用心理批评方法时,从“最初的努力不够成熟”,“不很在行地使用这种工具”,“对心理学只有皮毛的了解”,或者无限扩大、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种工具,都会出现不够完美的地方,这种“急于上阵的必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消失,“心理学投射到文学上的光辉便逐渐耀眼起来”。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尤为难免。由于一些新的方法所赖以建立的各种新的科学在我国不甚发达,或者译介工作一时跟不上来,也妨碍我们从精神实质上掌握和认识某种流派和方法。当然,也存在一种情况,那种徒有其表、无实质内容变化的新名词大串联,概念大换班,或者将并不艰深的道理说得曲里拐弯,叫人受累费解,这也是读者指出来的,是一种不怎么高明的拼贴性的技术和技艺状态。我们的评论已经意识到并且想要摆脱这种状态。
新时期的评论经历了一个阶段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恢复与正名之后,进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的横向引进、移植和借鉴。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似乎又转入了新的一轮从技艺走向艺术的发展过程。从关闭到开放、到引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方法的多样,观念的变革、丰富和发展,增强了我们接近文学、认识文学的手段与本领。恩格斯晚年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里,曾经作过这样的反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这封信里,他提出了认识事物要看到它“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总的合力”的思想。可以说,恩格斯提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留给了后人。在文学上,社会批评和经济分析决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也应当探索影响文学、影响作家作品的那个无数的“力”。从这种严格意义上说,对象有多么丰富,方法就有多么丰富,文学有多么丰富,方法和观念就有多么丰富,它们是不可能穷尽的。过去,由于闭塞、单打一,忽然听到五种批评模式、六种主要批评趋势,感到耳目一新。
我是从一个侧面,根据自己接触的零零星星、挂一漏万的现象,谈一点粗浅的想法。新时期的文学评论,是足够别的同志写出更多有分量的文章的。
同前述作家的情况有些类似,还有许多中、青年作家自身的“创作谈”,它们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些“创作谈”,是作家们整个身世的叙述,是他们从动荡岁月闯荡过来的心的诉说,是他们投出羊鞭、走出艺术大门的如实记录。他们不必像在作品里那样,间接地表现自己,而是直抒胸臆,感情抒发与理性反思并茂,具有较高的评论价值和艺术价值。张承志发表在《十月》上的、后来收在《老桥》集子里的《后记》,何士光的作品集《故乡事》的《后记》以及其他一些作家如陈世旭、叶文玲、韩少功、古华写的创作谈,都是这类受到读者好评的文章。在另一种情况下,作家发表的言论,是他的作品的评论的辅佐材料。比如1985年底,张承志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黄泥小屋》和评论《美文的沙漠》,我们可以把后者看成评述前面那个中篇的钥匙。《黄泥小屋》里缓缓律动着的几个人物的意识和动作,那依傍大地、挣扎底层的劳动者的欢悲苦乐,以及由此升华出来的生命的抗争与迁徙,还有,通贯全篇的如音乐如画的场景和旋律,如果离开了他主张的“美的叙述”,离开了他的独创的、不可模仿、不可翻译的美文,离开了他那如骆驼突人沙漠的“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就无从把握那个作品的“魂”。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西方一些学者也在考虑,某种批评方法固然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文学现象,但是由于倡导者的片面性、自成一家的排他性以及在使用上停留在技术、技艺状态,这些方法的覆盖面和生命期各不相同,甚至影响它们的效用。比方说,一般说来,现实主义创作适于采取社会学方法和道德批评,形式主义批评较宜应用于诗歌,精神分析法有利于分析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荣格的理论对解读深受神话影响的作品有利,此外,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各有用途。这些方法可以长期在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加以绝对化,这样,排斥了他人,也就排斥了自己。因此,韦勒克说:“在我看来,批评的任务,亦即方向,应该是把某一艺术品作为整体加以分析和评价。”一些西方学者看出了这个问题。文学评论要从技术、技艺上升到艺术,必须是一种整体的、富于感情的把握,要把方法融会到这种整体把握中去。弗?克鲁斯在1980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指出了这一点,他说:“20世纪文学批评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在实质上似乎都是严格地以经验,甚至以技术为基础的。”他对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作了回顾和对比:“文学批评目前所处的位置和它在18世纪末的情况大体相似,当时是感情表现精神向布瓦罗和蒲伯的权威挑战。现代的作品分析若是已经到了霍尔姆所预言的那种‘古典主义复兴’的程度,对此那些想和文学有着更为直接、密切关系的人也许不会欢迎。”因为,方法的使用不当,那种冷冰冰的技术、技艺状态会“堵塞感情的注入”。
由此,想起评论的存在和独立价值。它不是一张节目说明单,如果是那样,节目看完了也就可以扔掉了。评论是继作家提供给读者的人生画面的“第二次曝光”,里面有评论家的见识,闪烁着和跃动着他那一颗灵心。它是说得明白的、清晰的,但这是不够的。它是科学的,解说公允的,这也是不够的。它必须是艺术的。因为即使是科学的,也终归是可替代的,可更迭的,惟有艺术,才蕴含永恒的、生生不息的魅力。科学家烙印着认识,艺术家烙印着生命和灵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谈到东山魁夷关于北欧的绘画,说这是两者的邂逅,北欧与东山,缺一不可。他说:“北欧的大自然风物的存在,是东山的幸福和愉快;而东山的存在,难道就不是北欧大自然的幸福和愉快吗?”这说得真好。仿此推理,优秀的作家因为有优秀的评论,而结下了那份难得的缘分,读者也因之而获得和结下新的缘分。这就是评论存在的真正价值。
区分艺术与技术或技艺,就像区分艺术家与能工巧匠一样,一直为人们注意。现在看来,关键的还是看艺术家、评论家能否以自己的人格、情怀、艺术感觉对待事物,把新的观念、方法加以融会,在评论中体现一种完整的、富于感情的把握。刘再复是最早介绍和提倡新的研究方法、主张拓展思维空间的评论家,他的评论同其他一些优秀评论家的作品一样,决不是某些方法的机械搬用。他评论刘心武、王蒙的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以心灵的辩证分析见长,又贯穿社会批评、道德批评,甚至包括某些人指出的原型批评。然而,使他的评论获得新鲜感的,让读者得到再创造的艺术感受的,是他流贯评论中的两种感情意识:对历史、对民族、对艺术的忏悔意识,对自我的忏悔意识。他对刘心武写的谢惠敏这个人物的三重悲哀(灵魂的扭曲;扭曲而又不感到痛苦;反过来又以自己的扭曲压抑另一个灵魂)的分析,对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的两层心灵痛苦(西方文化挑动了他的痛苦,西方文化的虚幻又给他以无尽的诱惑与折磨)的分析,就是例证。他自己也随着作品和人物一起反思,他说他受到《班主任》的“启蒙”,“好象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他的坦率、热情、无遮掩的自我主张,以及包括反思、批评、悔悟在内的深广的忧患意识、忏悔意识,使得他的评论具有一种吸引人、撼动人的艺术力量。
新时期开初几年,那是感情勃发的时代,思想奔放的时代,评论和创作一样,就像两股清流,深深吸引读者。“伤痕”与反思,既贯注于创作,也贯注于评论。例如王蒙、钟惦裴等人的评论,既是作者久郁心头的痛苦和情思的喷发,也是推断说理与声情抒发相交织的机杼之作。其中,是他评,还是自诉,是写评论,还是在创作,很难分得清楚。于是,人们认为,有的作家的评论文字所博得的叫好不亚于他们的个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