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出路”——解读挣扎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命运
- 格式:pdf
- 大小:175.98 KB
- 文档页数:2

旷日持久的“逃离”——从《逃离》探求“出走”女性的“归路”作者:李伟华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李伟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摘要: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的《逃离》中,卡拉的“逃离”是对男权话语下自身需要无法满足的环境的逃离,并企图重建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环境。
然而作为女性,要完成这一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
卡拉最终体验到女权主义导致的人格分裂的悲剧境遇。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出走”的她而言,基本生理需求、安全和归属感都面临危机,自我实现需求就不再那么重要。
最终“约拿情结”占领了她的身心,她拒绝了解救者的指引,再次回到丈夫的身边。
家庭环境造就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依靠别人来解救自己,自己都不会答应。
在一切都显得无药可救的时刻,小说最后“出走”又“归来”的山羊充当了他们共同的神域,和他们发生了某种精神上联系,就像自然与灵性一样。
使他们最终勘破人性造就的幻象,摆脱罪恶感、界分感和二元对立,直接体验自身内在的神性,体验到巨大的幸福、解脱、连贯和至真,长久以来的无谓争吵也烟消云散,彼此释然,找到了自我的本真,从根本上结束女性内心旷日持久的“逃离”,走向了更好的心灵归宿。
关键词:“出走”女性;人格分裂;需求层级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长青哲学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85-02一、男权话语下的女权主义:“问题”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初期,对文学女性的“出走”甚为关注,因为女性出走是女性反抗意识的直接表现。
出走的经典形象当推娜拉,她不甘当丈夫的玩偶,为寻求自身的价值愤而出走。
女权主义存在许多问题。
“女性总归要和男性打交道,纯粹脱离男性的女性也是不可思议的。
女性不只是女人,首先也是人,打破或冲出了男权樊篱,不能陷入女性中心主义,女权主义的追求应当和人类的进步相一致。
”女权主义运动越深入发展,早期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反抗女性形象越具有误导性,她们的反抗精神难能可贵,但反抗方式并不能保证女性反抗成功并获得解放与幸福,甚至往往导致女性的悲剧。


从安娜、娜拉出⾛看⼥性的觉醒与反抗⼥性解放的问题,我们过去在探讨,现在在探讨,将来我们还会将其讨论下去。
不论是东⽅还是西⽅,⼥性解放都受到⼈们的关注,尤其是⼀批崇尚⼥性解放的作家,他们⽤⾃⼰在⼩说中塑造的⼈物,揭⽰男权社会对⼥性的不公,社会对于⼥性的冷酷与残忍。
他们⽤⼀个⼜⼀个鲜活的⼈物来为⼥性哭诉,为⼥性表达要求解放的迫切愿望,为⼥性寻求解放的道路。
压迫虽由来已久,但是东西⽅⼥性都做着同样的事情,要求解放。
也许觉醒程度不同,反抗的⼒量与⽣活的时代不同,但是都存在着觉醒与反抗,为各⾃的解放⽽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
本⽂将以安娜、娜拉两个⼥性为代表,阐释⼀下⼥性所受的压迫,⼥性想⾛出牢笼的觉醒,⼥性所作的反抗,与对⼥性解放道路的理智探寻,并就⾃我解放对⼥性提出了三⽅⾯要求。
在安娜与娜拉的⽐较中,不少研究者将他们⽐作⿊暗王国的新⼥性,他们的反抗精神对于⼥性的解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年易⼘⽣的⼀部《玩偶之家》在⽂坛引起轰动,然⽽这位策划⼤师却并没有给出出⾛⼥⼈的结局。
为此,⼈们颇多猜测。
对于娜拉出⾛后结局的分析与研究,⼤体分为三个:有的⼈认为娜拉五路可⾛,出⾛后就是饿死的下场;有的⼈认为娜拉回来的可能性很⼤,负⽓出⾛,⽓消后继续回归家庭⽣活;有的⼈认为娜拉的下场就是堕落,沦为娼妓。
鲁迅在《娜拉⾛后怎样》⼀⽂中指出:“娜拉或者是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只⼩鸟,则笼⼦⾥固然不⾃由,⽽⼀出笼门,外⾯便⼜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痹了翅⼦,忘却了飞翔,也诚然⽆路可⾛,还有⼀条,就是饿死了。
”或许对于娜拉,⼈们还算是宽容,相⽐较于安娜,⼈们似乎并不⼗分看好。
毕竟安娜为了爱情背叛家庭,违背了⼀直以来传统道德所尊崇的所谓“妇道”。
⼈们对于安娜持同情⼜责备的态度。
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安娜,不难发现⾝为贵妇的安娜的⽃争反抗远⽐娜拉复杂的多,托尔斯泰的家庭思想和⽭盾困惑也⽐易⼘⽣更为深刻⼴泛。
![从“娜拉式出走”透视萧红的女性意识[权威资料]](https://img.taocdn.com/s1/m/ac77c3e9f605cc1755270722192e453610665bed.png)
从“娜拉式出走”透视萧红的女性意识摘要:萧红曾被鲁迅誉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也是东北作家群中是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
敏感多情、离经叛道、柔韧倔强、才华横溢、痛苦挣扎演绎了萧红传奇的人生,“娜拉式出走”是她砸碎封建枷锁、选择新生的武器,在多次的出走中找寻幸福的出路。
尽管她头破血流,但壮士断腕的勇气令人赞叹,那一首首描写北方人觉醒的战歌是我们咀嚼的精神食粮。
她用敏锐的视角画出了国人灵魂的自画像,那里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困顿彷徨和超越,她从婚恋自由、人格独立、自我实现中体现女性意识成长的心路历程,写作之路成为她解构男权中心、获取话语权、重塑女性形象的生命之路,鼓舞女性从萧红的“娜拉式出走”中关照自身,寻求女性解放的方舟。
关键词:娜拉式出走萧红女性意识写作之路自我实现“妇女意识”先由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49年出版专著《第二性》中提出。
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演说《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出了“妇女意识”的文艺观。
中国封建社会抑制人性的自由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处于失语的状态,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传播,冰心、冯沅君、卢隐、石评梅是第一批觉醒的女作家,萧红是其后涌现出的女性作家,她以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为切入点,《王阿嫂的死》、《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都以力透纸背的笔法控诉了女性的悲惨命运,透过女性苦难揭示国民性的根源,找出疗治顽疾的“药方”来。
离家出走,遵循内心的呼唤――婚恋自由。
萧红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除了祖父的唯一关爱外,她倍受歧视与冷眼、束缚与压抑。
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期间她经历逃婚、纠缠不清、对簿公堂、遭人遗弃等痛苦挣扎过程,未婚夫汪恩甲因无力还钱抛弃怀有身孕的萧红后,在旅店老板的讨债和威吓中度日的萧红陷入了绝境,是萧军将萧红挽救于水火之中,萧红才真正迈出了离家的坚定步子,踏上寻找婚姻自由的道路。

论欧茨短篇小说《何去何从》中的女性悲剧文章分别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角度分析并揭露了女主人公康妮的悲剧成因。
结果发现,康妮的悲剧既来自于男性对女性的忽视和压制,也来自于其他女性的排挤和女性角色自身的被动。
文章将为从女性群体自身的弱点来寻找女性悲剧的动因提供有益的启示。
标签:《何去何从》;女性悲剧;男性;女性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美国当代文坛上最有名的女性作家之一。
尽管她声称自己并非女性主义作家,却在很多长篇和短篇小说中都力图表现女性人物的生活和命运。
文学评论家格莱格·约翰森认为:“在她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对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一直持着同情而又独立的观点。
”[1]《何去何从》是欧茨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它初次与读者见面是在1966年,此时正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鼎盛时期。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少女康妮这个女性世界中最弱小的一分子的悲剧故事展示了欧茨在自己文学创作早期不成熟不全面的女性主义观。
本文试图解析文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共同作用下的康妮的悲剧成因。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
一天晚上,当康妮在和她的朋友在商场闲逛时,她遇见了一个“长着蓬松的黑头发,开着一辆漆成金色的旧敞篷汽车”[2]的男孩。
不久之后的一天,当康妮被家人独自留在家中时,男孩哄骗威胁康妮走出家门。
在故事结尾,康妮服从了男孩的意志,而她的悲剧也随之展开:她将面临着被这个恶魔般的男孩和他的朋友伤害的可能性。
她的悲剧虽直接由阿诺德造成,但也间接由她的家人和她自己引起。
康妮悲剧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男性的忽视和压制,以及女性自身的排挤和被动。
一、男性:忽视和压制这篇小说中出现的男性人物包括康妮的父亲、男孩艾迪、阿诺德·弗兰德以及他的朋友艾利·奥斯卡。
他们均与本小说的女主人公及其最终的悲剧命运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三人之中,与康妮的悲剧关系最为密切的男性人物为康妮的父亲和男孩阿诺德。

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月亮与六便士》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一、本文概述《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作家毛姆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深刻的人物刻画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了无数读者。
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为了追求艺术理想而抛弃世俗生活,最终走上精神崩溃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尽管这部作品以男性艺术家的视角展开,但其中的女性角色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月亮与六便士》中女性角色的形象,探讨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命运与抗争,揭示作品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
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将首先梳理作品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包括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艾米、模特勃朗什以及画家施特略夫的妻子。
接着,我们将结合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这些角色在男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迫,以及她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还将探讨作品如何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女性如何寻求自我救赎和成长的可能。
通过对《月亮与六便士》中女性角色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女性主义视角下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推动社会对女性权益的进一步认识和尊重。
二、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概述《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形象丰富多样,涵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性格特征。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些角色不仅仅是情节的推动者,更是对当时社会性别观念的一种反映和挑战。
我们来看看小说的女主角布兰奇·沙垂尔。
她美丽、温柔,是许多人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然而,布兰奇也是社会传统观念的牺牲品,她将自己的全部价值和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最终却因为无法满足对方的期望而走向悲剧。
布兰奇的命运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期待,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在这种期待下所承受的压力和束缚。
除了布兰奇之外,小说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角色,如斯特里克兰的太太、画家艾米·劳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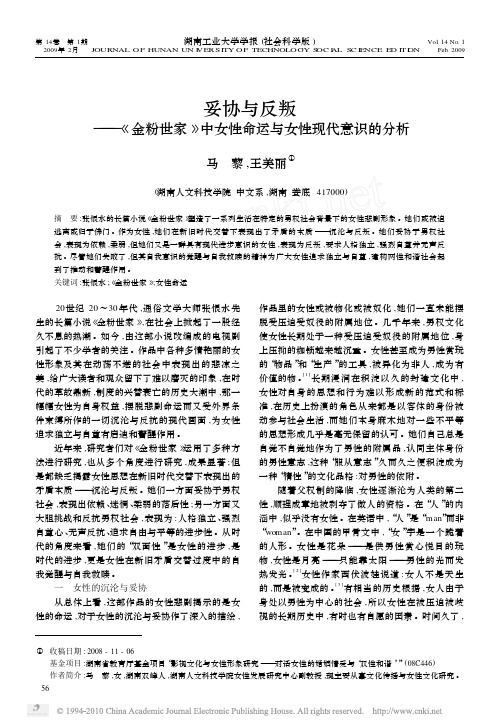
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马 藜,王美丽①(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417000)摘 要: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特定的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悲剧形象。
她们或被迫逃离或归于佛门。
作为女性,她们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了矛盾的本质———沉沦与反叛。
她们妥协于男权社会,表现为依赖,柔弱,但她们又是一群具有现代进步意识的女性,表现为反叛,要求人格独立,强烈自尊并无声反抗。
尽管她们失败了,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救赎的精神为广大女性追求独立与自尊,建构两性和谐社会起到了推动和警醒作用。
关键词:张恨水;《金粉世家》;女性命运20世纪20~30年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热潮。
如今,由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作品中各种多情艳丽的女性形象及其在动荡不堪的社会中表现出的悲凉之美,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时代的革故鼎新,制度的兴替衰亡的历史大潮中,那一幅幅女性为自身权益,摆脱悲剧命运而又受外界条件束缚所作的一切沉沦与反抗的现代画面,为女性追求独立与自尊有启迪和警醒作用。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金粉世家》运用了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也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成果显著;但是都缺乏揭露女性思想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的矛盾本质———沉沦与反叛。
她们一方面妥协于男权社会,表现出依赖、迷惘、柔弱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又大胆挑战和反抗男权社会,表现为:人格独立、强烈自尊心、无声反抗、追求自由与平等的进步性。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她们的“双面性”是女性的进步,是时代的进步,更是女性在新旧矛盾交替过度中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救赎。
一 女性的沉沦与妥协从总体上看,这部作品的女性悲剧揭示的是女性的命运,对于女性的沉沦与妥协作了深入的描绘,作品里的女性或被物化或被奴化,她们一直未能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
几千年来,男权文化使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

文学界..摘要:《孤恋花》是《台北人》中最为催人泪下的一篇,其中娟娟与五宝两个不幸酒女的遭遇,深刻表现了在男权话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境遇。
本文主要从父权、夫权、男权社会三方面解读《孤恋花》中白先勇为女性唱出的一曲哀歌。
关键词:男权;《孤恋花》;女性哀歌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1)07-0056-02白先勇是台湾六七十年代很有影响的一位作家,在文坛上素有短篇小说“奇才”的盛誉,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作为其最高成就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更是唱出了一个旧时代的挽歌,作为一位“末路英雄”的子弟,白先勇奏出了一曲曲“没落贵族的挽歌”,但远非如此,他的出名主要源于其塑造的形态各异的近八十位女性形象。
他自己也说过:“有些人批评我写没落的贵族,我觉得不是,我什么都写么。
在《台北人》里,老兵有、妓女有、酒女有、老佣人、老副官、上的下的,各式各样的人”,在他写的一系列社会沦落者的作品中,《孤恋花》无疑是其中最为催人泪下的一篇。
《孤恋花》中两个不幸的酒女形象五宝和娟娟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物,五宝可以说是娟娟的前身,娟娟是五宝的再现。
“五宝是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的,卖到万春楼,才十四岁”,后来被“壮得像只大牯牛”的军人疏拢,最后“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
而娟娟也是命苦异常,母亲是疯子,自己十五岁就被生父强奸。
沦为酒女后,她由于性格荏弱,逆来顺受,受尽了酒客、嫖客的摧残蹂躏。
后来,凶狠残暴、毫无人性的黑社会头目柯老雄霸占了她,对她不仅随时随地滥施淫欲,而且一再残酷殴打,弄得她“全身便是七痨八伤,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完全成了柯老雄变态性行为的牺牲品,但最终她反抗了,一个深夜,当柯老雄对她进行例行的蹂躏、斥骂和厮打时,他举起了一双“黑铁熨斗”,向柯老雄的头颅“猛捶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灰白的脑浆流得一地……”,虽然报仇了,但她也疯了。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了简·爱的出走和复回。
简·爱出走的根本原因是她不愿意做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他者,出走是她为争取女性自由和独立身份做出的抗争;简·爱的复回也并不是出走的失败,出走前的简·爱和复回后的简·爱有着质的不同,简·爱的复回是女性自由和独立身份的进一步巩固,是简·爱女权意识的升华,对女权主义的发展更是一种启发。
关键词:简·爱;出走;复回;女性主义一、引言《简·爱》问世160多年以来,始终是英语小说中拥有广大读者的一部作品。
这部小说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人生低头的坚强女性,创造了英国小说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和社会都采取了独立自主态度的女性形象。
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时至今日,这部小说依然是文学批评界的宠儿,每年都有新的批评文章问世。
随着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简·爱》成为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批评文本。
女性主义批评家深入挖掘了文本中的独立女性意识和简·爱的双重人格意识,阐释了女作家的双声话语和挑战父权制的微妙写作策略。
女性主义批评家大都聚焦于简·爱的独立反抗意识,对简·爱从桑菲尔德府出走的选择大加赞赏。
与此同时,对于最后简·爱重新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大家则众口一词,一致认为这是作者对社会的妥协,也是简·爱对自我经过千辛万苦换得的独立女性身份的放弃,因此是小说的一大败笔。
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结局表达了对男人的力量和权利的敬意(林树明,2004:30)。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肖瓦尔特提到《简爱》时也曾批评道:“19世纪那些独立的女主角,通常都被设计为最终都回到了男人的大氅和安慰的避难所”(Showalter,1973:13)。

浅析鲁迅笔下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摘要: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刻画了众多女性的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笔者认为尤为耀眼的是那些为追求个性自由、为中国解放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女性们,本文就此对这些女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鲁迅;作品;新时代;女性鲁迅作品中铁屋子里的女性形象中,有一种女性是那么的勇敢、那样的与众不同,他们就是新时代的女性形象,他们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已经觉醒的女性。
一、追求个性自由而奋起反抗的女性《伤逝》中的子君就是这一类女性形象,子君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涓生在一起,她不顾社会、家庭的阻挠,毅然离家出走,自主自由地与涓生结合了,为追求幸福,她敢于向一切传统势力挑战,在家庭社会的阻挠下,她勇敢地反抗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多么勇敢,多少坚决的宣言啊!为了维持和涓生的同居生活,眼看涓生已经用去了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她觉得有义务分担这个责任,立刻把全部首饰卖去,又逐日活泼起来,通过这些细节,作者塑造了一个坚定、大胆、勇敢的中国女性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她毫不动摇毫不妥协的反对封建的觉醒精神。
子君是有工作能力的,不过在她所处的那个社会里,不管资产阶级叫得怎样响亮,职业仍然没有向女子开门,于是子君开始学习做家务,做起了真正的家庭妇女,和涓生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了。
涓生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子君也领会地点点头,然而却倾注着全力管好家务。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个时候,涓生失业了!为了生活,只得四处贴广告,托人,译书等,在一个狭小的住所里,子君汗流满面地做饭,涓生手忙脚乱地译书,这样的生活,不能不让人乏味而厌恶起来。
生活的逼迫,使得他们已焦头烂额了,无暇谈天来相互沟通了。
终于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对于追求个性的子君来说,这无疑是致命地打击,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鲁迅在一九二三年底作了一次有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娜拉看透了自私的丈夫的嘴脸,要摆脱自己的傀儡命运,毅然离家出走,剧作到此戛然而止,娜拉从丈夫的家庭出走,娜拉的背叛行动即震惊了男权社会,震醒了昏睡中的女性,她说“我首先是一个人!”这跟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一样是多么响亮的宣言啊!这在女性受压迫,受压抑的环境下是多么富有挑战性啊!但是娜拉即使从家庭出走,等待她的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试析自我意识的突围与文化批判—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现象_85991试析自我意识的突围与文化批判—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现象[标签:来源]论文关健词:出走自我意识文化女权主义论文摘要:“出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显示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自觉对束缚自我的“文化圈”突围,从而又完成了对文化的批判。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以“出走”为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
自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专号”,将《娜拉》带给中国文坛后,“娜拉的出走”便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
呈现于文本显现为“出走”现象的普遍化、“出走”形象的多样化以及“出走”主题的深刻化。
“出走”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一现象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质,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的裂变史和文化批判史。
(一)文化是民族结构中最厚重、最稳固的层次,这种特性使文化常常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的变动常常需要外力的批判与颠夜。
文学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它在承担一定的社会拯救功能的同时就不可能不承担一定的文化批判功能。
因此文学价值的获取就更多地来自于批判所期待的自我与文化的和谐状态。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冲撞: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次改革开放。
西方文化的传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此消彼长,至今尚无结局。
这中间文化的斗争表面看来水波不兴,其实内部已潜流暗长,斗争的激烈同样让人惊心动魄。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严格地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一种文化批判,是用一种文化批判另一种文化。
但这种文化批判方式只是一种外部批判,极易成为浮于形式的改头换面,而不能深人血液与骨位去改变传统文化的疲疾。
一方面,传统文化经历了致命的冲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而使其又有些积重难返。
因此,这种批判极易引起文化的混乱,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一、对《王氏之死》的解读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选取冯可参《郯城县志》、黄六鸿《福惠全书》、蒲松龄《聊斋志异》节选为材料,描述明末清初,山东郯城县当地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税收,遗产争夺,以及官府和地方势力矛盾与冲突等小而普通的事情。
像王氏这样的下层百姓的遭遇在那个年代是不会引起官府和地主的关注,官府关注的只是赋税有没有按时交纳,而地主关注是哪户人家又欠了田租,这些底层人民只是些淹没在大历史中的小角色而已。
因此,史景迁一改往日史学精英史的研究,从小人物着手,通过一些普通民众的故事来揭露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这本书共有六章,第一、二、四章对明末清初农村社会的矛盾进行描写,包括土地分配、农民由于超经济负担的赋税而寻求豪门大户的庇护来抗拒国家的税收,地方府衙则通过种种方法与豪门大户争夺税户,以及地方势力与官府的恩怨引起的武装冲突。
第三章关注农村妇女寡妇问题,按照当时法律,丈夫死后,若妻子不改嫁,则由儿子继承遗产,为了钻法律的空子,家族中觊觎遗产的人便千方百计的毒害继承人。
第五、第六章描写了郯城县村妇王氏的生活,以及她不堪忍受现实而逃跑,最终却落得被处死刑。
王氏的例子代表了当时妇女大众的命运。
在她们身上,凝结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悲哀。
用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映射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本书的精髓。
二、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一)处于农民阶级的妇女必定承受来自阶级的压迫山东郯城频繁地受到自然灾害、农民起义、政权更迭以及盗匪贼寇的磨难,无钱无权无地位的平民百姓在灾祸面前显得格外孤立无援。
而课税徭役繁重、地方恶霸横行、商人趁火打劫、士兵作威作福、地主包揽代理无疑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村女妇女受到更大的剥削,通常农村女性一方面同男性一起分担沉重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着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对此书中也有所照应:蒲松龄写到1640年有一次大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一个男的为了生活,就把他的妻子卖给店铺的老板,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可以被丈夫随意买卖,没有人身的自由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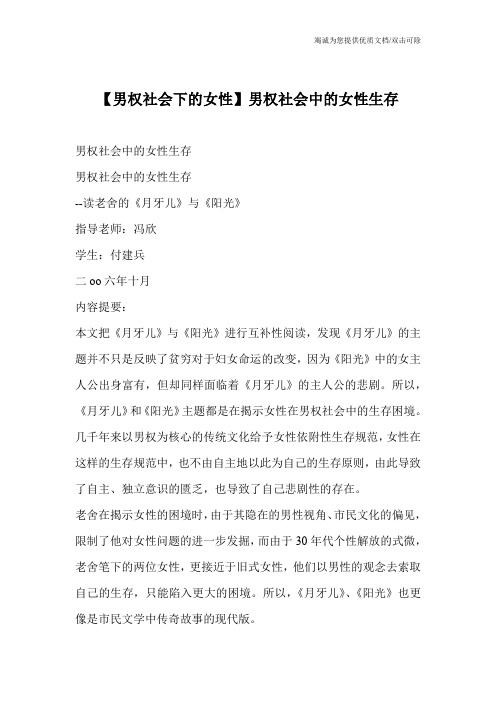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读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指导老师:冯欣学生:付建兵二oo六年十月内容提要:本文把《月牙儿》与《阳光》进行互补性阅读,发现《月牙儿》的主题并不只是反映了贫穷对于妇女命运的改变,因为《阳光》中的女主人公出身富有,但却同样面临着《月牙儿》的主人公的悲剧。
所以,《月牙儿》和《阳光》主题都是在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几千年来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给予女性依附性生存规范,女性在这样的生存规范中,也不由自主地以此为自己的生存原则,由此导致了自主、独立意识的匮乏,也导致了自己悲剧性的存在。
老舍在揭示女性的困境时,由于其隐在的男性视角、市民文化的偏见,限制了他对女性问题的进一步发掘,而由于30年代个性解放的式微,老舍笔下的两位女性,更接近于旧式女性,他们以男性的观念去索取自己的生存,只能陷入更大的困境。
所以,《月牙儿》、《阳光》也更像是市民文学中传奇故事的现代版。
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读老舍的《月牙儿》与《阳光》《月牙儿》是老舍1935年由散失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的一段加工而成的。
这对一个惯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以现实主义而称道的作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应该说尝试是成功的,作家本人也感到庆幸,并接着写了姊妹篇《阳光》,收在《樱海集》中,于1935年8月由人间书屋出版。
《月牙儿》因其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浓郁的抒情笔调,贴切的象征意蕴赢得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青睐,但具有同样风格的《阳光》却相对被冷落。
也许,正由于此,限定了对《月牙儿》主题探讨的视野,仅将其定位于贫穷与女性命运的关系上,也限定了对老舍妇女观的进一步挖掘。
如果将《月牙儿》与《阳光》进行互补性阅读,不难发现:如果说前者是贫穷与女性,后者则是富有与女性,但两者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及其行为与思想却具有相同性。
由此,我们认为,《月牙儿》的主题并不只是贫穷。
饭,独立与依附等问题,也是富有的女性阶层所面临的。


大 众 文 艺93摘要:父权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女性在其统治下逐渐失去自我意识,异化成父权制的工具, 维护父权统治,压迫自己的同胞。
本文通过分析《呼兰河传》中的两类女性形象,结合萧红的经历,阐释父权制下女性循环往复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父权制;《呼兰河传》;女性形象;悲剧人类社会由母系进入父系,父权制就成为一种社会结构绵延数千年,世代传承。
所谓父权制,即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俗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女性应该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1]在父权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统治下,女性被奴役成女奴,女性逐步丧失自我意识并顺从父权意识形态,同时,父权制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判断。
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女性很难挣扎与反抗。
特别是那些从父权制中获益的女性,她们不仅努力维护这种专制制度,而且异化成男权社会的工具,剿杀自己的同性。
即使有女性反抗父权制,她们最终都会被病态的父权制冷酷无情地折掉飞翔的翅膀,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萧红的《呼兰河传》完成于1940年12月,这部散文化的抒情小说被茅盾评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2]作品主要以营建氛围和叙事为主,没有丰满的人物形象。
萧红写出了两类女性的悲剧命运:一类是以小团圆媳妇婆婆为代表的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另一类是以小团圆媳妇为代表的父权制传统铁蹄下的间接受害者。
结合作品,本文将对小说中的两类女性形象作以下分析:一、父权制传统的传递者小说开篇阶段人物塑造篇幅较少,首次出现的女性形象是一位母亲,只因孩子说猪肉是瘟猪肉,就拾起烧火的叉子打孩子,孩子向祖母求救,祖母却因杨老太太看着,也要面子地“用力地在孩子的屁股上哐哐地打起来”;有五个孩子的三十多岁女人因孩子抢大麻花,也拿烧火的叉子向孩子奔去。
在这里,萧红没有正面描写她们的不幸,而是用第三者的视角写出了她们对待孩子的方法,我们没有感受到她们积极的母亲形象,相反,却体会到她们在父权社会下的“男性化”,她们对孩子只会用暴力教育,在别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