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乡土文学(一)
- 格式:docx
- 大小:15.32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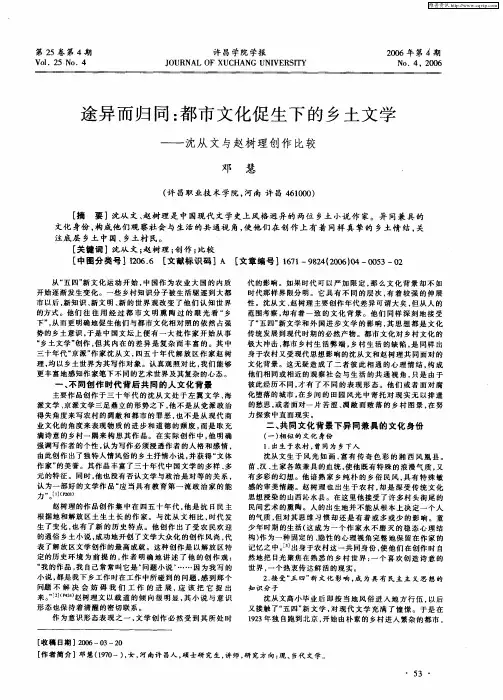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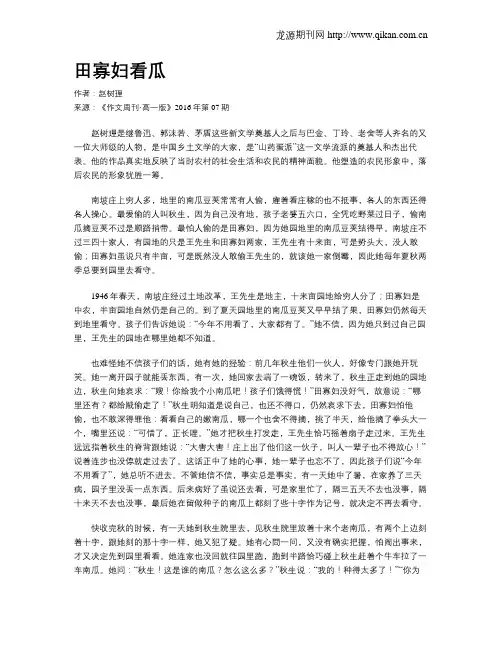
田寡妇看瓜作者:赵树理来源:《作文周刊·高一版》2016年第07期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家,是“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
他塑造的农民形象中,落后农民的形象犹胜一筹。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
最爱偷的人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
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
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1946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
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
孩子们告诉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
”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地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像专门跟她开玩笑。
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东西。
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舍不得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
”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
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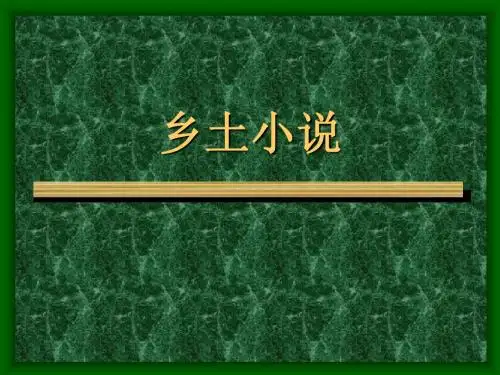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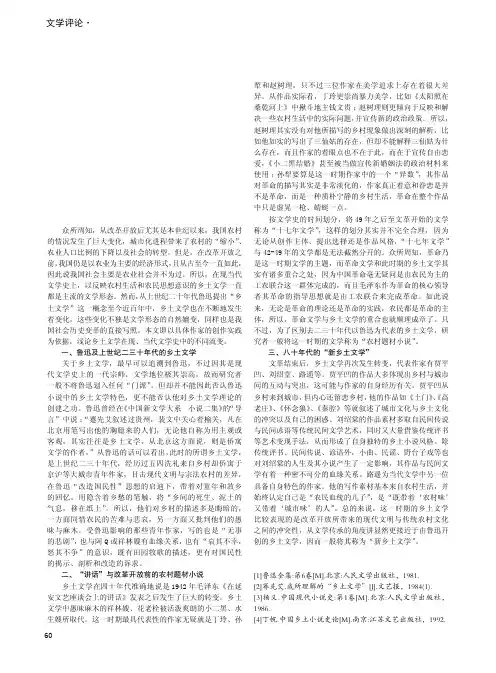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论乡土文学在现、当代的不同流变王静 辽宁财贸学院摘 要:五四伊始,乡土文学就成为我国文学的重要组成,且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乡土文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流变,第一次是发生在四十年代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小说的转变,第二次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从农村题材小说到新乡土文学的转变,而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变迁也在乡土文学的两次流变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关键词: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文学;流变作者简介:王静(1982.3-),女,辽宁省兴城市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60-01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农村的“缩小”、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社会的转型。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仍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因此说我国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并不为过。
所以,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意识的乡土文学一直都是主流的文学形态。
然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至今近百年中,乡土文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不独是文学形态的自然嬗变,同样也是我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直接写照。
本文即以具体作家的创作实践为依据,浅论乡土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不同流变。
一、鲁迅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关于乡土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鲁迅,不过因其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文学地位极其崇高,故而研究者一般不将鲁迅划入任何“门派”,但却并不能因此否认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文学特色,更不能否认他对乡土文学理论的创建之功。
鲁迅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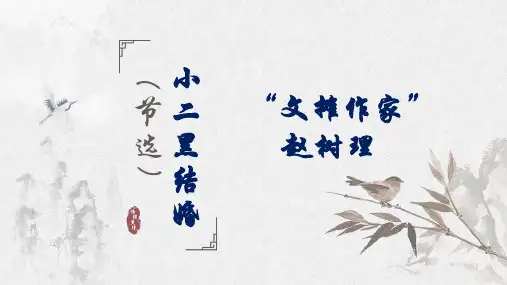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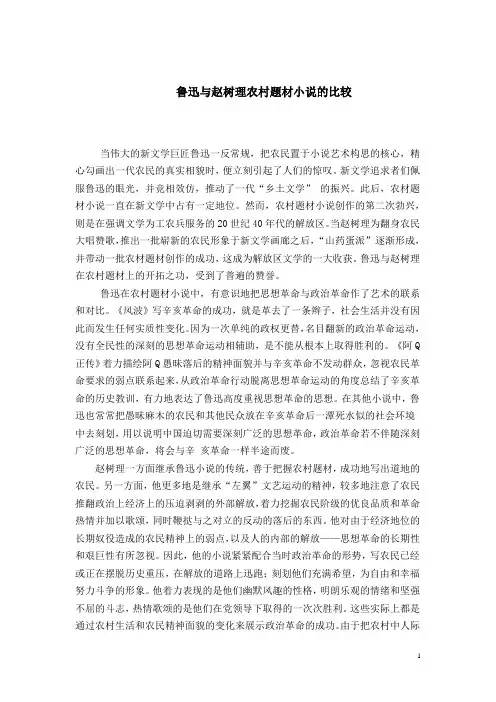
鲁迅与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的比较当伟大的新文学巨匠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
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 的振兴。
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
然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二次勃兴,则是在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
当赵树理为翻身农民大唱赞歌,推出一批崭新的农民形象于新文学画廊之后,“山药蛋派”逐渐形成,并带动一批农材题材创作的成功,这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大收获。
鲁迅与赵树理在农村题材上的开拓之功,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鲁迅在农村题材小说中,有意识地把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作了艺术的联系和对比。
《风波》写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革去了一条辫子,社会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因为一次单纯的政权更替,名目翻新的政治革命运动,没有全民性的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相辅助,是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的。
《阿Q 正传》着力描绘阿Q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并与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忽视农民革命要求的弱点联系起来,从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的角度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力地表达了鲁迅高度重视思想革命的思想。
在其他小说中,鲁迅也常常把愚昧麻木的农民和其他民众放在辛亥革命后一潭死水似的社会环境中去刻划,用以说明中国迫切需要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深刻广泛的思想革命,将会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而废。
赵树理一方面继承鲁迅小说的传统,善于把握农村题材,成功地写出道地的农民。
另一方面,他更多地是继承“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较多地注意了农民推翻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剥剥的外部解放,着力挖掘农民阶级的优良品质和革命热情并加以歌颂,同时鞭挞与之对立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
他对由于经济地位的长期奴役造成的农民精神上的弱点,以及人的内部的解放——思想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所忽视。
因此,他的小说紧紧配合当时政治革命的形势,写农民已经或正在摆脱历史重压,在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刻划他们充满希望,为自由和幸福努力斗争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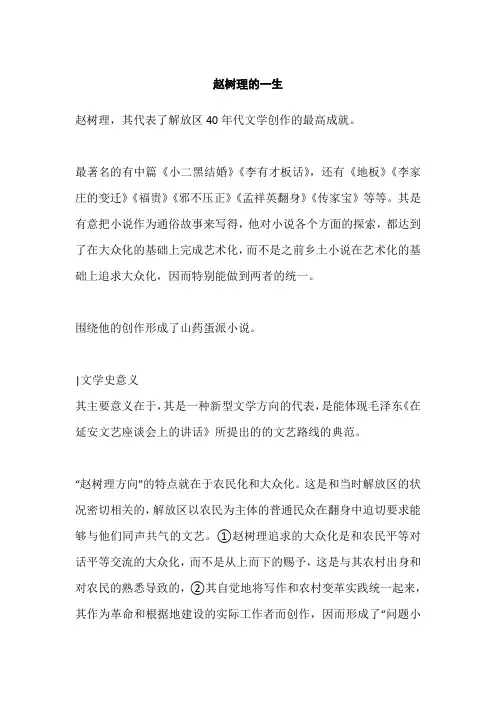
赵树理的一生赵树理,其代表了解放区40年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最著名的有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有《地板》《李家庄的变迁》《福贵》《邪不压正》《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等等。
其是有意把小说作为通俗故事来写得,他对小说各个方面的探索,都达到了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完成艺术化,而不是之前乡土小说在艺术化的基础上追求大众化,因而特别能做到两者的统一。
围绕他的创作形成了山药蛋派小说。
|文学史意义其主要意义在于,其是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的文艺路线的典范。
“赵树理方向”的特点就在于农民化和大众化。
这是和当时解放区的状况密切相关的,解放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在翻身中迫切要求能够与他们同声共气的文艺。
①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和农民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大众化,而不是从上而下的赐予,这是与其农村出身和对农民的熟悉导致的,②其自觉地将写作和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其作为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工作者而创作,因而形成了“问题小说观”,自觉追求反映党的农村建设工作中的偏差以及对农民的影响。
其局限性则是,前者使得赵树理过分排斥知识分子,过分排斥西方文学,于是文化修养不足,视野也比较狭小,后者则使得小说和党的农村工作紧密联系,在党的农村工作出现偏差时,问题小说的模式就出现了言不由衷等危机。
不过在这一时代,其创作的局限性还没有显示出来。
|赵树理创作的特点分成两部分吧,内容上和形式上。
①内容上,赵树理塑造了一批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首先是背景上,其小说的背景是在晋东南的农村,具有鲜明的民俗色彩地方色彩,而如今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作为总体终于翻身了。
赵树理将这整个背景其作为一种社会景物,提供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环境,具有空间上的地方性,也具有时间上的时代性,这共同构成了其小说具有的现实性,其具有实效性,能够紧密配合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
而在写乡土题材,尤其是写农民上,其继承了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但是不是以人道主义的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写理想中的田园牧歌,或者写农村黑暗,而是能够更进一步,直接同农民对话,展示农民的精神风貌及其面对的矛盾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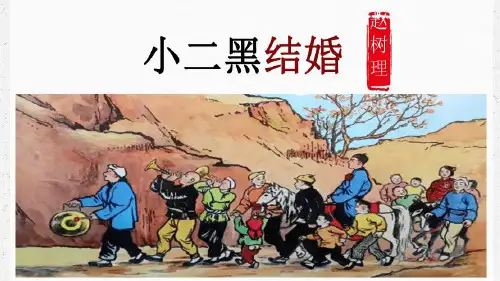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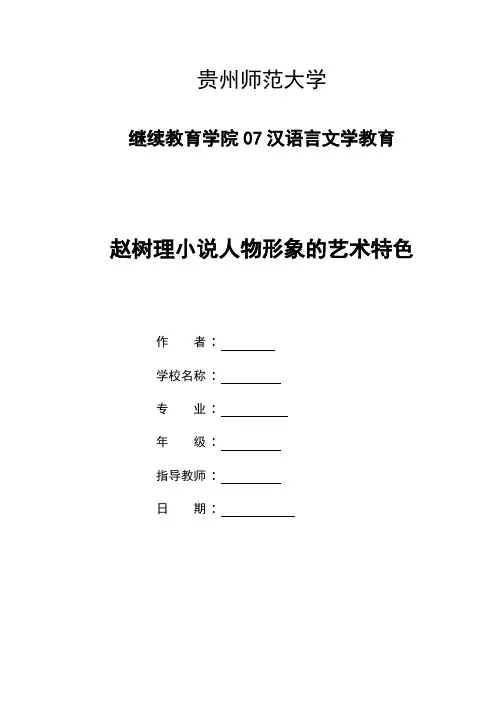
贵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07汉语言文学教育赵树理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作者:学校名称:专业:年级:指导教师:日期:目录摘要 (Ⅲ)1赵树理简介 (1)1.1赵树理家庭背景 (1)1.2赵树理的社会经历、作品及影响 (1)2.“山药蛋”派的开创 (2)3.赵树理小说的涉及面 (3)3.1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3)3.2恋爱婚姻习俗 (4)3.3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5)4.赵树理的艺术成就 (5)4.1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5)4.2艺术风格 (5)4.2.1通过情节发展自然展示人物性格 (6)4.2.2 通过语言、形体动作展示人物心理,揭示人物性格 (7)4.2.2.1人物语言 (7)4.2.2.2形体与语言相结合 (7)4.2.3 通过细腻的外部描写展现人物性格 (8)4.2.3.1描写人物外貌 (8)4.2.3.2写景 (8)4.2.4用辩证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9)4.2.4.1辩证手法 (9)4.2.4.2现实主义手法 (10)后记赵树理惨死的前前后后 (11)参考文献 (13)浅议赵树理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摘要赵树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是继中国文坛鲁迅、郭沫若、矛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大家”,是“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的奠基人和杰出领袖。
在他的作品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面貌,而且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
他的小说经常采用农民群众民间语言,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落后人物的成功塑造。
这些人物分别通过情节发展,语言、形体动作,细腻的外部描写及辨证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现实主义新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奠基人三仙姑杰出领袖1、赵树理简介1.1赵树理家庭背景赵树理,现、当代作家。
原名赵树礼,笔名野小、吴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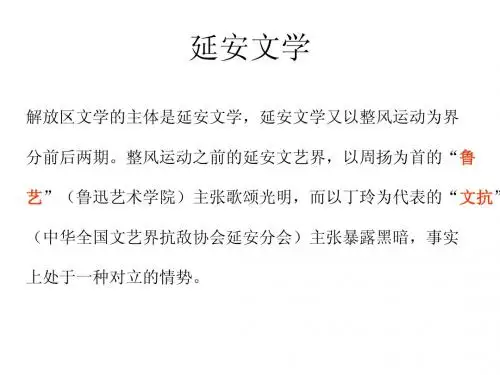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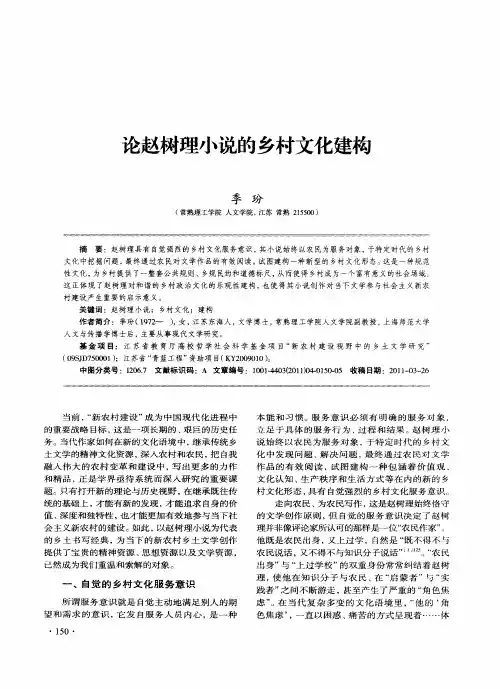
赵树理与乡土文学(一)
当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时,他虽然没有具体限定“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意义,但我理解,“赵树理方向”首先在于他的文学的大众化方向和鲜明的倾向性,因此,“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就是“乡土文学”的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尽管并非赵树理的首创,但真正达到在主观上自觉的为农民写、写农民、给农民看的“文的自觉”则确要从赵树理算起。
这不仅表现在题材的自觉、语言的自觉、人物塑造的自觉等文体创造方面,更主要地表现在赵树理创作意识的自觉。
他主动的有清醒意识的让文学去接近劳工大众,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阅读范围和审美情趣,诱导他们的思想意识朝着合理的方向靠近,而远离封建糟粕的侵蚀。
由此可见,“赵树理方向”并不是“被动的迎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上”。
这从他“一步一步地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的表白中,就可看出他的文学志愿和目标。
所以,仅仅认为“赵树理方向”停留在“文学的第一个层次上”的说法,其实是并不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历史现实。
试想,没有把大众的情趣引导到健康的文学阅读上,而放任于封建糟粕中,谈何向文学的“第二层次飞跃”?这不有点让古代的人去奢想宇宙飞船一样,强人所难吗?由此、我们评论一位作家要近可能的放到一定的历史现实环境中,重点考察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而不必强求他“应该怎样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把赵树理摆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渊源流变中,进而把握他的位置和历史贡献。
一
在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见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他虽然还主要是对“五四”后期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的深刻概括,但对“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已有所揭示。
在国际,“乡土文学”则出现于19世纪末,步利特·哈特等在美国的倡导。
在台湾,“乡土文学”最早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台湾语文与乡土文学》,原始定义为描述大众生活并使用大众语言,即方言。
“乡土文学”的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及随之而来的作家创作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的。
在此,“乡土文学”是指那些真切地展现了作者故乡的农村和小乡村的风土民俗,寄托、表现著作者的乡情,着力于描写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诞生包含着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第一批乡土文学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始终扎根于乡土文学的作家,而是一批离开了故乡,在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人。
鲁迅当初在给“乡土文学”命名时,强调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大概也包含着对人们的这种提醒。
他们正是在经受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冲击之后,再重新回过头来看自己幼时生活过的偏僻乡村,才获得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角的,从而突破了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的局限。
幼年乡村生活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差”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文明和愚昧、科学和迷信、民主和法治、变革和保守等的差别,而当他们力图剖析故乡农民苦难的根源时,他们所借助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受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
“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反观’与‘反思’”。
因此,如果当时作家始终囿于故乡的生活,而不走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异地”去,他们就很难获得对本土封建宗法社会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力量,也就很难设想会诞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
由此可见,“乡土文学”虽然散发着泥土气息,但现代意识犹如不可遮掩的灵光放射着它的光泽。
这就使“乡土文学”从一诞生始,就站到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而不沉没于乡村的文化气氛中。
不过,当时的“乡土文学”同当时的变革还有着某种脱节。
比如20世纪二十年代那场席卷中国的农民革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农民群众由此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觉悟,变革意识的高扬,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农村而引起的一次大爆发。
然而除了彭家煌的《今昔》等极个别作品外,这种农民
的“自觉的阶级觉悟”并未在“乡土文学”中得到反映。
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如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蹇先艾、王统照、许杰等基本上是在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上作着开掘,即使偶有显示出农民觉醒动向的作品,也只是前进到表现农民的重压之下的个人反抗,如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惫者》等。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侨寓者”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感同身受到乡村土地上的巨大变化,而且也在于他们在“侨寓者”的生活环境中的思想状况。
他们所感受到的,还主要是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意识上的觉醒,而他们落魄、苦闷的处境,悲观恨世的感触,使他们格外容易注意起农村的破败、农民的麻木,而对于中国农村正在萌生的现代意识,似乎感受不深了。
有的乡土小说,如冯沅君的《劫灰》会把农民的反抗斗争写成“土匪”的“浩劫”。
作者经历过那段乡村生活,但却不能理解,这和作家的立场观点不无关系。
这种作家主观方面的限制和作品思想性的局限到了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乡土文学中出现了某些变化,这就是由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到反映农民的觉醒、反抗的主题进步。
左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环境。
同时,民主主义色彩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俄苏文学和东北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影响进一步渗透到这一文化环境中来。
这就使得无论是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老作家,如许杰、王鲁彦、彭家煌等,还是左联时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新人,如叶紫、沙汀、艾芜、蒋牧良等,其创作对于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反映都出现了一些新因素。
一些作品中,农村依旧是破败,农民的生活也依旧充满着悲剧色彩,但这一切都有了更为清晰的时代背景,如王鲁彦的《李妈》、吴祖湘的《樊家铺》等;在另一些作品中,时代终于推出了觉醒、反抗的一代新农民,如叶紫的《丰收》、许杰的《七十六岁的祥福》、沙汀的《老人》等,在这些新农民身上,“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升华;还有些作品,如艾芜的《山峡中》、蹇先艾的《倔强的女人》、芦焚的《巨人》等,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对立中,着力于展现农民嫉恶如仇、讲求信义、追求自由等美德。
上述种种,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意识对作家思想的渗透和进步。
稍后一些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由于创作环境的特殊,又没有像关内乡土文学那样政治化,因而较多地保留着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一些特色。
如有着浓重的乡思乡愁,有着对民俗风情的生动描写。
不过,当时乡土文学的作家不是如王鲁彦们生活在异地异城,他们就朝朝朝夕夕生活在沦于敌手的故土,感同身受着家乡民族和阶级反抗的呼声,同时,他们的创作又较多地借助了俄罗斯和一些被压迫民族(如匈牙利、波兰、朝鲜等)的农民题材小说的影响。
这使得他们在反映家乡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上,表现了比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更及时的感应时代脉搏的生活和艺术敏感,起码有以下几点的变化是明显的。
首先,一般乡土文学中充溢的乡思乡愁,在东北乡土小学中还渗透出一种浓烈的思恋、怀念祖国的情绪,小说中的一些农民人物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祖国不可分,如梁山丁的《挛生》。
其次,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而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基本是在反封建的主题上作着开掘的话,那么东北乡土文学却是在法西斯文网森严的严酷环境中,用富有血肉的历史画面,深刻表现了反帝的主题,如王秋莹的《矿坑》、《小工车》等。
再次,同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品中“哀其不幸”的悲凉气氛比较起来,东北乡土文学则因传达出农民在民族灾难中的反抗的觉醒而使一些作品的色彩较为鲜亮,如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袁犀的《风雪》、疑迟的《乡仇》、王秋莹的《血债》等。
上述这些都表明东北乡土文学作家开始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上来把握揭示农民的命运,而这不仅来自于他们所受的左翼文学、俄苏文学的影响,也是现实生活给予他们的,因为东北沦陷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大大促使了东北土地上的民族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获得现代文明意识的集中体现。
纵观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及东北乡土文学的发展概况,文学的主题开掘有了令人可喜的拓展,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社会现实的反映,表现了农民正在逐步觉醒的历史进程。
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也明显地存在着某些缺陷,而这正是有待于完成的历史使命,它不得不现实地推到了解放区作家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