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的现实主义分析
- 格式:docx
- 大小:36.87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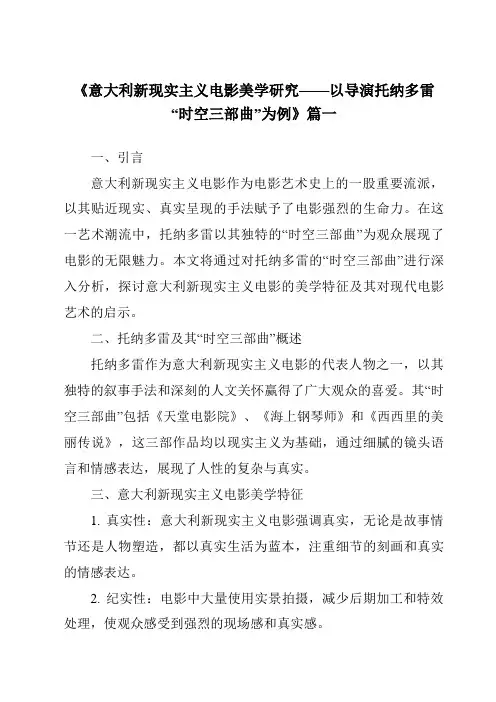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研究——以导演托纳多雷“时空三部曲”为例》篇一一、引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为电影艺术史上的一股重要流派,以其贴近现实、真实呈现的手法赋予了电影强烈的生命力。
在这一艺术潮流中,托纳多雷以其独特的“时空三部曲”为观众展现了电影的无限魅力。
本文将通过对托纳多雷的“时空三部曲”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及其对现代电影艺术的启示。
二、托纳多雷及其“时空三部曲”概述托纳多雷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其“时空三部曲”包括《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作品均以现实主义为基础,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情感表达,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特征1. 真实性: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强调真实,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以真实生活为蓝本,注重细节的刻画和真实的情感表达。
2. 纪实性:电影中大量使用实景拍摄,减少后期加工和特效处理,使观众感受到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3. 人文关怀:新现实主义电影注重人性的展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以平凡的视角表达深刻的情感。
4. 故事情节的丰富性:虽然以现实为基点,但电影在叙事上并不拘泥于传统模式,而是通过丰富的情节和细腻的镜头语言来展现故事。
四、托纳多雷“时空三部曲”的美学分析1. 《天堂电影院》:电影通过对小镇电影院几十年的变迁的讲述,展示了人与时代的共同成长与记忆,将一个普通的影院变为一个小镇的记忆缩影。
托纳多雷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真实呈现,展示了人们对于家乡、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
2. 《海上钢琴师》:电影以一个天才钢琴师的一生为线索,通过其与爱情、友情和音乐的关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在电影中,托纳多雷运用了大量的纪实性镜头和真实的情感表达,使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3.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电影以二战时期的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

第10期NO.10福 建 教 育 学 院 学 报2018年10月October.2018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摘 要:文章主要采用空间叙事学的理论对奥尼尔的经典剧作《毛猿》进行解读,文中的五个空间:船舱、五马路、监狱、世界产联和动物园的依次出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每个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封闭空间,当文中的人物以“闯入者”的形象进入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空间,便会打破空间原有的平衡,带来悲剧的后果。
奥尼尔不仅描写了人失去归属的痛苦,同时也描写了人在经历失败后仍不断追寻自我的勇气,表现出作者对人性复归的寻求与不惧失败的尝试。
关键词:《毛猿》;空间叙事学;封闭空间;“闯入者”;自我追寻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84(2018)10-0104-04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1888-1953)在美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目前为止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一位美国剧作家。
《毛猿》(The Hairy Ape,1922)是奥尼尔的一部表现主义代表作,展现了普通劳动者在西方社会中失去归宿的重要社会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奥尼尔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对文中的人性异化、宗教意识、找寻归属等主题展开分析。
近年来由于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尝试用空间理论对此文本进行分析,有从空间理论视域下分析文中隐喻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或从西方后殖民主义角度研究他者空间,但是还没有从空间叙事学的角度对文章进行分析。
在现代戏剧中,空间的叙事功能突出。
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指出:“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节奏,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
”[3]《毛猿》正是利用空间的变换来推动文中的叙事进程,文中船舱、五马路、监狱、世界产联和动物园依次地出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中国故事与东方情感的表达摘要:王小帅作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影片更多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从1993年《冬春的日子》到2019年的影片《地久天长》,在他二十几年的创作历程中,影片一以贯之带着东方情感的表达。
《青红》《我11》《闯入者》表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发动的“三线建设”工程,三部影片都是反思那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保守固执,扭曲的价值观,用温和的创作态度缅怀一代人的峥嵘岁月。
关键词:女性形象;母题;东方情感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3-0090-03(东北石油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黑龙江大庆163318)于喜峰∗∗∗第41卷第3期绥化学院学报2021年3月Vol.41No.3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Mar .2021收稿日期:2020-09-30作者简介:于喜峰,东北石油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高五级,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在中国电影导演代际划分的行列里,王小帅被公认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第六代电影人基本上没有受过"文革"的影响,经历了旧体制、旧观念的消融,目睹了各种新念的产生,他们是抗拒归纳的一代,所表现出来的电影大多标新立异。
王小帅的电影风格多样,独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影像风格。
“三线三部曲”包括《青红》《我11》《闯入者》三部影片,三部影片在三线大背景的基础上表现了王小帅影片中独特的叙事风格与其文化指向。
纵观王小帅的影片,《地久天长》的创作思路和情感表现等方面与“三线三部曲”有诸多互文性表达,“互文性”是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的,是指“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的著名观点,这也是最早的关于互文性的解读,对于研究电影文本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照王小帅的影片,不难发现,《地久天长》中有对于“三线三部曲”的互文性表达,影片吸收了以往影片中人物性格塑造思路、关于“逃离与归来”母题的阐述,以及温和的创作态度,影片一脉相承无处不打着他个人化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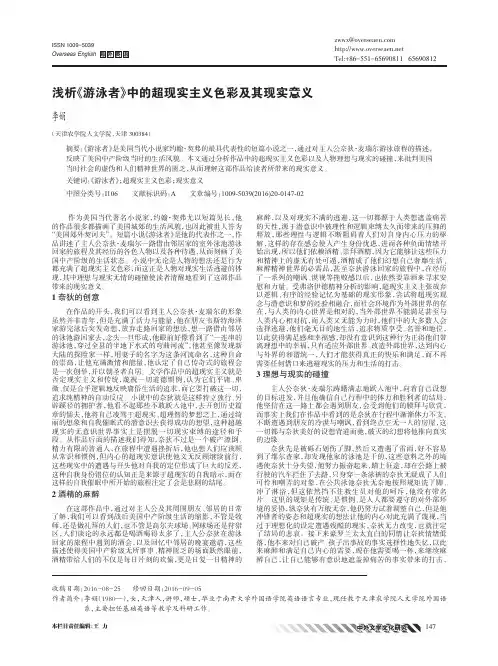
一一一一一一一中外文学文化研究本栏目责任编辑:王力浅析《游泳者》中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及其现实意义李娟(天津农学院人文学院,天津300384)摘要:《游泳者》是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契弗的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通过对主人公奈狄·麦瑞尔游泳旅程的描述,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当时的生活风貌。
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以及人物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来批判美国当时社会的虚伪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匮乏,从而理解这部作品给读者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游泳者》;超现实主义色彩;现实意义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39(2016)20-0147-02作为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契弗尤以短篇见长,他的作品很多都描画了美国城郊的生活风貌,也因此被世人誉为“美国郊外契诃夫”。
短篇小说《游泳者》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奈狄·麦瑞尔一路借由邻居家的室外泳池游泳回家的旅程及其经历的各色人物以及各种待遇,从而刻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小说中无论是人物的想法还是行为都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而这正是人物对现实生活逃避的体现,其中理想与现实无情的碰撞使读者清醒地看到了这部作品带来的现实意义。
1奈狄的创意在作品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奈狄·麦瑞尔的形象虽然并非青年,但是充满了活力与能量,他在朋友韦斯特海泽家游完泳后突发奇想,放弃走路回家的想法,想一路借由邻居的泳池游回家去,念头一旦形成,他眼前好像看到了“一连串的游泳池,穿过全县的半地下水式的弯曲河流”,他甚至像发现新大陆的探险家一样,用妻子的名字为这条河流命名,这种自命的崇高,让他充满激情和能量,他认定了自己传奇式的旅程会是一次创举,并以朝圣者自居。
文学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就是否定现实主义和传统,蔑视一切道德惯例,认为它们平庸、卑微、仅是合乎逻辑地反映庸俗生活的追求,而它要打破这一切,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


电影照进现实——现实主义电影的态度与精神电影照进现实——现实主义电影的态度与精神作为一种精神风潮和艺术形式,电影一直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现实世界。
现实主义电影作为其中的一个流派,通过真实地展现生活和社会现象,以真实和直接让观众深入思考与反思。
本文将探讨现实主义电影的态度与精神,并解析它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现实主义电影,顾名思义,追求真实和客观。
它关注生活中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故事,力图以现实的方式揭示社会存在的问题。
与虚构电影相比,现实主义电影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富有代表性。
它在呈现社会现象和问题时展示了真实的面貌,使观众对现实有了更直观的感知。
现实主义电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在现代电影史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战争之后》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电影,他的导演安德烈·泰尔克斯基用尖锐的视角揭示了战争的摧残和人性的扭曲。
这部电影以真实的细节和近距离的镜头,展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人们在逆境中的生存状态。
通过这种真实的描绘,观众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战争给个体和整个社会带来的伤害,激发了对战争的深思和平和的追求。
而在当代,像是《千钧一发》和《娘娘腔》这样的电影,则着重展现了现实主义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
《千钧一发》通过讲述一个城市的环保问题和对生态的破坏,呼唤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
而《娘娘腔》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探究了性别认同和社会压力。
这些电影以现实主义的刻画揭露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与偏见,引起了广大观众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除了展示社会问题,现实主义电影还秉持着审视人性和探索人类存在的重要任务。
电影《波兰源泉》以真实细腻的方式描绘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善恶。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安德烈·韦达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在这样一种细腻的描绘中,不仅对战争感到愤怒和悲伤,更对人性和人类价值感到深深的思考。
现实主义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所呈现的现实,更在于激发观众的思考和行动。
《闯入者》的现实主义分析王小帅第12部作品《闯入者》入围第39届多伦多电影节和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其依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点推出肉体之外的“潜意识”,试图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方式,摆正现实与梦境的差别,以此展开心灵救赎。
《闯入者》较好的把迷茫文青气、“老三线”生活和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以冷峻的姿态从人物内心出发,使用戏剧化手法,探析虚实幻灭的“闯入者”。
一、戏剧情境铺陈——“空间”韵味影视艺术除去镜头语言的表达,核心部分需戏剧性叙事来搭建传奇故事,所有故事脉络都应围绕戏剧情境来铺设。
“戏剧情境是促动戏剧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
”1同时,戏剧情境“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特定情况、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
”2导演采用小景别的交代方式,外加空间范围的局限(即老邓一家所在生活社区、学校、养老院、公车),以凸显主人公狭隘、阴郁生活的日复一日。
同时,老旧的居民区和现代化居民楼、公交车和现代轿车、家庭和养老院、北京和老三线,形成四组完全对立的空间环境,试图对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展开探讨,进而推出时代更迭的后遗症,如此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大社会背景对人心的导向。
纵观影片中的环境,渗透着萨特禁闭剧的影子。
当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只有喘息声从无人应答,进而促使老邓一家处于被动的猜测状态,随影视时空流转,接电话者张军和邓美娟的往昔罪过都通过对话表现在观者面前。
大军接后,推测是因工地纠葛,想到自己没给工人钱的事件。
而老邓开始疑神疑鬼的推测是自己死去的老头子,终感知是一份关于老赵多年前罪责的讨债,老太太强悍的内心在无人作答的电话前坍塌,对老赵一家的忏悔成为影片表现的重要情节。
能够说此类外在情况和环境的铺设,对影片情节的搭建具有直接促动作用。
戏剧情境书写中还有更值得推敲的环节,即故事的人物关系设定,这也是故事讲述的基石。
回看具有王小帅标签的影片不难发现,人物关系谱表现去复杂化,《闯入者》也延续简单人物关系原则。
围绕居住在北京的一位年过六旬丧偶老太(文革时期的“施暴者”)讲述,观者看到老邓以忙碌的状态掩饰过往的不堪,却难掩心魔的不停拷问,同时在老邓的现实生活中言行举止透着特殊时代寄予的强权纠察之使命感,这种盲目监督的责任感成为剧中所有矛盾的症结所在。
其次,老邓两个儿子的定位选择依旧延续“小人物”的命题特质:大军忠厚沉稳,事业家庭均走在小康道路,是婆媳之间的润滑剂,扮演着时代的附庸且一切行动都在中规中矩中;小兵性格叛逆,以做网店为生的同性恋者,也是老邓强统治最无能为力的失败案例,其身上散发着现代社会与“红色”年代的观点对垒。
除此之外,影片还塑造了处在暗处的角色——红帽少年(老赵的孙子),给予少之又少的对白来增加神秘气息。
同时创作者巧妙地赋予他“红帽”形象,来引出红色时代尘封多年的往事谜底。
仅几组人物设定,影片的故事即能表达出创作者对其内涵的推敲,这应该归因于小帅导演多年创作经验的把控。
影片《闯入者》依靠戏剧情境的铺设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谱,为观者搭建起通往剧情深处的时空桥梁,进而持续探索事件蔓延过程中迸发的“空间”韵味。
跟随人物关系的交错牵制,使老邓心理感知也越发清晰,成为引导剧情悬念的关键所在,也促使戏剧性越发丰满。
二、戏剧悬念预设——“红帽”危机剧作者根据人物关系及戏剧背景制造出观者期待的情节变化,带来人物命运的难以捉摸,在此基础上依据冲突的展开,在悬念到来时为某一社会问题发声,使观者跟随悬念的起伏变化感受这个社会问题的好与坏、善与恶、情与理。
电影《闯入者》里的悬念设置在影片开始就与主题契合度极高,随情节发展精彩碰撞持续升级。
于影片前端:1.多次电话铃声的响起,接起后无人应答,最终传来“嘟嘟……”的挂机声。
几组镜头后观者开始注意到这个并非偶然的叙事导引,到底电话那头是什么人,又有怎样的起因。
2.邓老太一家相聚老大张军家吃团圆饭时,剧情安排神秘人第一次出现,王璐闻门铃声开门见一大堆垃圾涌入,暗处行为冲突升级至正面,当张军和张兵楼梯、电梯双重堵截时,与张兵同电梯而下的红帽少年开始隐隐显现出不安定因子,同时少年的鸭舌帽遮住面部也为剧情悬念的铺设贡献了一些主观价值。
3.进而又通过一组夜间向老妇家扔砖头的镜头,开始从事件发起者邓老太的主观视角看到带红色帽子的陌生少年。
《闯入者》通过画面静态表达,一遍遍神秘电话、垃圾堵门、扔砖头事件的敲击,营造出神秘且不安的特殊情况和环境,为影片扣上悬疑的基调,一股如涓涓细流涌入的“闯入者”形象在电影开端即显现悬念契题效果。
同时,邓老太与少年造就虚实模糊的意识跌宕。
1.邓美娟留少年住在家里,给他做狮子头,把对家人无处安放的爱部分地放在了他身上。
不过邓美娟不知道,这是“引狼入室”。
2.“红帽少年”操刀欲砍、撕碎照片、老太街头追寻少年的镜头书写,刻意模糊现实和想像间的界限,此处剪辑也跳脱开慢速行驶的节奏,影片的戏剧张力所以而增强。
不过,悬念的铺设如此之多,又该以怎样的感知体验抛出解决悬念时的社会深思呢?《闯入者》在片尾采用区别于片头的非常态化静态审视,转以快节奏逼近事实真相,以从“红帽少年坠楼”事件引发社会深思。
当红帽少年落地时,有种危险因子坠落的寓意,同时导演有意把红帽少年设置成红色记忆的代表,他的落地徒增起邓老太罪责问鼎,即祈求原谅的遥遥无期,传达出个人的消失并不能泯灭整体的无意识,所以一人的悔悟也是无法去除伤痛或者换回和解。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邓美娟表情复杂的脸上,存有更多的还是茫然的韵味,社会在进步,不过总有这么一群或一批人处于迷茫状态,他们努力前行却依旧找不到救赎的方向。
观影体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来自视听感受,而真正带领观者进入影视世界的还是悬念生发的浮城迷事。
小帅导演在《闯入者》的悬念塑造上,采用大量跟镜头制造“鬼视点”持续寻求影视语言的悬而未决;又在故事创作的结尾,打破国内大团圆结局的观影期许,采用欲罢还休的问题悬置,真正把戏剧悬念推向高潮。
“红帽危机”带给人们深思的人心救赎,预警还在继续。
三、戏剧动作对垒——“心境”变迁传统戏剧样式中台词和舞台动作是组接戏剧的精髓,所谓人物形象都是在言行举止中或正面或相反的显露个人色彩和内心情绪。
影视作品中戏剧动作的描摹同样适用,以下将从形体动作和言语动作展开《闯入者》的剖析,探寻动作背后的心境变迁。
“一般说来,冲突就是未获得解决的戏剧性动作。
”3影视艺术里言语动作在推动情节和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打开话语制造矛盾冲突。
影片中有一句魔咒一般的象征话语,即“狮子头”系列,老邓总想给家人做狮子头吃,甚至老邓把自己心心念念想做给家人吃的狮子头做给红帽少年。
“狮子头”被创作者披上如狮子般霸道的压制,同时又处于尴尬的位置,两家人面对这道菜时的选择也在细微体现出家庭环境的殷实与窘迫差别。
而未谋面的“闯入者”以电话骚扰,张军接电话说是“刘胖子……”,邓老太接电话开口猜测“老头子……老赵……”,此处显然是用对白给出信息,引出事情的真相给予更大的事件悬念。
随期而至的张军和张兵兄弟俩的对话却发挥了与前者不同的效能,“老太太拼命的写他的揭发材料,后来……”。
此处对白与老邓和死去的老伴对话处相关联,“老黄打来电话说老赵去世后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通过以上对白交涉,知晓红帽少年是来寻仇的,由此,一股尘封了近40年的贵州回京风波在人物动作里才完全解码。
戏剧作品中把形体动作分为:纯粹外部动作和性格化形体动作。
诸如张兵翘小指往耳后撩头发、为男友细腻的解开围裙的动作,足以传达出老邓的小儿子是同性恋。
当年为了小兵能在北京落户一直难逃罪责,一辈子要强的老邓面对此刻被认为异类的小儿子,内心苦楚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对于邓老太代表性的戏剧动作能够用“一记耳光”、“一次下跪”、“两回奔跑”来总结。
来到贵州的老赵家,老赵妻子旭芳给邓美娟的“一记耳光”分明提示着:历史结下的仇恨没有因红帽青年的离开而轻易消解,也只能用扇耳光的方式图个片刻痛快。
而两家被仇恨渲染的代表见面,邓老太选择以下跪的动作求得片刻心境安宁,“这个跪”因为历史的纠葛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到底是认错、忏悔、祈求对方的理解、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或许都是,亦或许都不是,但毕竟暗示着某种和解的表象。
“两回奔跑”都是为了罪过,一是邓老太怀着善意且要赎罪的心情提醒老赵孙子有警察来抓他,这是邓老太的奔跑;二是少年为逃脱罪责摆脱警察而逃跑,这是红帽少年的奔跑。
事情却因少年不慎坠窗,造就赎罪的行动像悬置半空中的窗户,摇摇欲坠又后悔无期。
这样一段对过去的动作化剥离,我们看到的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少年在沉沦,老邓在悔恨中接近疯癫,警察无能为力,只能化作法律的执行者,而社会也秉承不了心理康复中心的使命,它只负责接纳和表现。
四、结论总来说之,《闯入者》前半部分被现实题材编织,涉及养老、同性恋、婆媳关系的问题;后半部分梦境交替错杂,超越现实主义的心理现实主义流露出拟态世界的心灵洗礼。
王小帅凭借自己以往电影里常用的平实表达方式,以碎片化的叙事细节,拼贴的电影内容,错落有致的把“闯入者”的主题意蕴表达丰盈。
其间戏剧化的情境营造,戏剧动作的传达,完成戏剧性的情节体现,悬念之紧凑,人物性格之鲜明,社会意义之深厚,都是《闯入者》戏剧化表达的强势伏笔,值得电影工作者认真推敲。
《闯入者》的现实主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