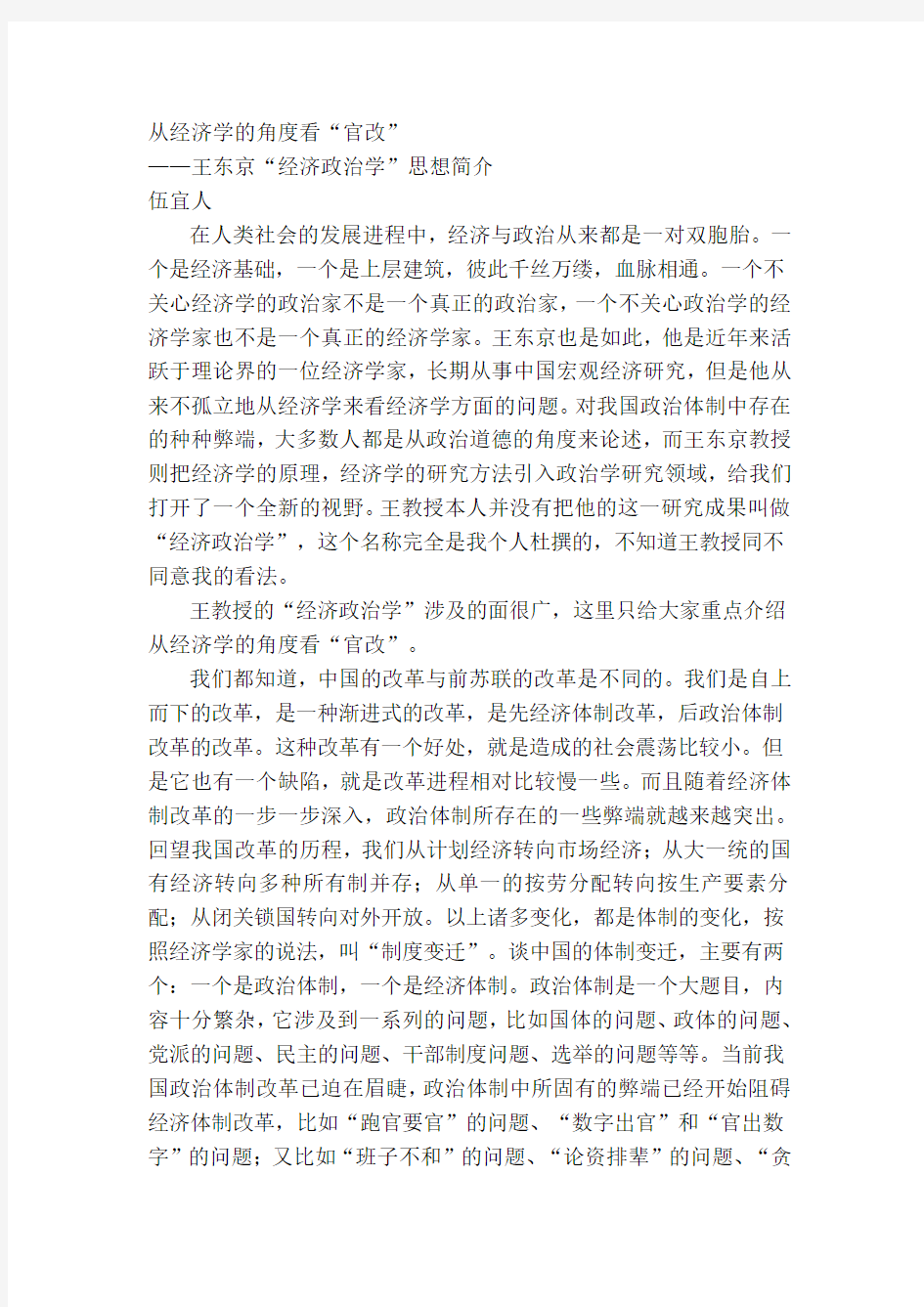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官改”
——王东京“经济政治学”思想简介
伍宜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济与政治从来都是一对双胞胎。一个是经济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彼此千丝万缕,血脉相通。一个不关心经济学的政治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不关心政治学的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王东京也是如此,他是近年来活跃于理论界的一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但是他从来不孤立地从经济学来看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大多数人都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论述,而王东京教授则把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王教授本人并没有把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叫做“经济政治学”,这个名称完全是我个人杜撰的,不知道王教授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王教授的“经济政治学”涉及的面很广,这里只给大家重点介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官改”。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的改革是不同的。我们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这种改革有一个好处,就是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缺陷,就是改革进程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步一步深入,政治体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就越来越突出。回望我国改革的历程,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大一统的国有经济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按生产要素分配;从闭关锁国转向对外开放。以上诸多变化,都是体制的变化,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叫“制度变迁”。谈中国的体制变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一个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一个大题目,内容十分繁杂,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国体的问题、政体的问题、党派的问题、民主的问题、干部制度问题、选举的问题等等。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弊端已经开始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跑官要官”的问题、“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问题;又比如“班子不和”的问题、“论资排辈”的问题、“贪
污腐败”的问题等等,这些已经严重障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大多数都只是就政治问题谈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跑官要官”屡禁不止?为什么会出现“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现象?为什么“班子不和”久治不愈?为什么“贪污腐败”愈反愈烈?王东京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是学派林立,复杂纷繁。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确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财产假定;与此大致对应的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的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
为什么说这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呢?因为200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便是如此。人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银行接连降息,目的是为了减少居民存款,扩大内需,但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不自私,任你银行利率怎么降,人们也会无动于衷;国债利率如何高,大家也不稀罕,那么政府刺激消费与投资,不就落空了吗?事实上,我们这几年降息对扩大内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正好说明,人是理性自私的。再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私奉献?因为人们客观上都是自私的,能做到无私不容易,所以对能做到无私的先进人物,理所当然要予以鼓励。但鼓励是一回事,客观存在又是一回事,假如我们把要鼓励的东西当作已经存在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最典型的就是把政府官员都当作无私奉献的圣人,所以长期
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如何呢?一是政府效率低;二是腐败屡禁不止。各国经验表明,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
关于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这个争议不大。市场经济所以强调要合理配置资源,就是因为资源稀缺,资源如果不稀缺,能敞开供应,需要多少有多少,那还要我们研究资源配置做什么?至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地球上的每一种资源都是有限的,科技再发达,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假如我所有的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你可以随便拿,那我也不是傻瓜,也不会努力工作,更不会积累财富,需要时到别人家里去拿好了。可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会积攒财富呢?那社会怎么进步?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保护个人财产,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有了上面的三个假定,再作进一步的推理,就有了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深刻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过剩?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倾向,故而生产有扩大化的趋势;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所以产品就会卖不出去。我们现在为什么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下我们的企业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人们的收入跟不上这种增长,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买方市场。
第二个原理即供求原理,这是由经济人假定和资源稀缺假定导出的,既然资源有限,人们又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了供求问题。当某种资源一定时,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价值规律。
第三个原理,等价交换原理。自从产生了社会分工,人们就难以自给自足了。我生产粮食,你生产布匹。可我需要穿衣服,你也需要吃粮食。粮食和布匹的产权又受到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我不能去你们家随便拿布匹,你也不能上我们家随便取粮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交换。并且这种交换还必须是等价的,交换双方都要感到合算才行。否则,有一方觉得吃亏,交易就达不成。所以,是社会分工和
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
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和帕累托标准。前两个方法,大家都很熟悉,而帕累托标准需要略作解释。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人们简称为帕累托标准。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态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态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举个例子,现在有20个人要过河,但只有一只小船且只能载19人,假如我们已经让19人上了船,船已满载,此时,我们就称之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如果再多让一人上船,就会因为超载而给另外19人带来危险,损害别人的福利。反之,如果本可以载19人的船,我们只让上18人,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因为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会损害到他人。
上面这三个方法,是作经济分析最常规的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厂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财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这些假定、原理、方法,不仅适应宏观经济分析,而且适应微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经济的放大,它也得服从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经济学界,尽管流派纷呈,学说五花八门,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些假定、原理、方法时,加进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或者是作逻辑推理时,各人的功力不一样,而基本的理论却万变不离其宗。
这讲的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我们下面再来看王东京教授是怎样运用这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解释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象的。
一是对“跑官要官”现象的解释
王教授的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不反对跑官。
国人崇尚做官,素有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虽反复强调:干
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可人们还是要削尖脑袋进机关、当干部。即使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择业观念已有大变,可是在很多地方,从政仍然是许多人的首选。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人们为何对做官情有独钟,一定要往“官道”上挤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人们乐于在政界摸爬滚打,主要受三样东西驱使:赢得尊重、获得收入和权力。其中,权力最为关键。有了它,不仅前两样东西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权力甚至有通天的本事,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所以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拜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控制了公共资源。对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他的,所以皇权至高无上。封疆大吏到七品县令,官印在手,管天管地管空气,说一不二,因此,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官”。当然,共产党的干部绝不是封建官吏,但人民给予的权力,同样是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计划经济时期,官员大笔一挥,可调拨物资,分配指标,下达任务,可谓字字千金。时至今日,越是市场经济欠发达、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方,人们的从政热情越高。在这些地方,机构精简难,公务员考试火,千军万马挤官道,大多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来的。
要想当官,就得“跑官”。从经济学上讲,市场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到商场购物,你一定会先弄清楚该物品的有关信息后,才肯付账。官场也是如此。握有选票的人,假如不了解你,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不跑,不向他们传递你的信息,他们如何选你做官呢?所以,跑官本身并没有错。无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做官都是需要“跑”的。不过体制不同,跑官的路径也就有所不同。有的往上跑,有的则往下跑。时下人们口诛笔伐的,就是那种只往上跑,不往下跑的跑官现象。
王东京教授认为,跑官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就看官帽子握在谁的手里。如果是上级任命下级,一言九鼎,老百姓人微言轻,说了不算,那么当官的人若往下跑,岂不是冒傻气。“官位”本来就是稀缺资源,求者若鹜,如此供应不足,你不往上跑,不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领导又没有长千里眼,哪知你是何方神圣?一旦调兵遣将起来,
自然就没你的事。经济学家说,制度高于一切。李瑞环同志也曾经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向上跑官,之所以屡禁不止,肯定是现行的选官制度有毛病。设想一下,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一锤定音,而主要是靠老百姓投票,规矩一变,你说他会往哪儿跑?多年来,我们总是埋怨某些官员宗旨观念不强,理想信念出了总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偏差,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冤枉,说到底是由于这种至上而下的选官体制造成的。
如果对这种“往上跑”的现象作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另一个奥秘。经济学分析,一个常规的方法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向上跑官所以在中国盛行,千古不易,还因其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因为跑官投入少,产出多,经济上很划算。以县级为例,干部提拔一般要过三关:组织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县委书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如果把常委会成员、列席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算在里面,总共不过10多人。只要盯住这几个人,经常跑一跑,如果有半数以上被“摆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这事就算大功告成了。而一旦官位到手,日后自然会有人往他那儿跑。屈指一算,跑官的诸多投资成本,与提升后的无期收益相比,只怕是九牛一毛,当事人即使不懂经济学,也能算得过这笔账的。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做官也得跑。小布什当年竞选总统时,还不是跑断了腿。不过人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跑官的路径与我们大不一样。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官场也是一种市场。政府就好比垄断经营的企业,官员好比经理,组织政府运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民类似消费者,用“投票”选择政府的“经理”,并由此决定自己将来享受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此一来,西方人跑官,得按市场规则办事。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官位”的呢?市场经济学崇拜的是自由竞争,对稀缺资源,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使用。这里的出价,当然不是让你掏腰包,而是要看你为民造福的本领,这有点象工程招标,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韬略,看你过去的政绩。可是老百姓对我素昧平生,怎知道你有多大能耐?于是,从政者要四处游说,要搞竞
选演说。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跑官,与计划经济体制正好相反,不是往上跑,而是往下跑,要争取让公众多投票。
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自有它的毛病,我们不必照搬。但公众多数人选人与少数人选人两种选官方式,我们一眼就可以分出优劣。解决往上跑官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我们当前的这种选官规则,让多数人选官,由老百姓选官,那么,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宗旨观念不强的问题等等就不难解决了。唯有如此,我们的干部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二是对“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现象的解释。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也是当前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央曾经三令五申要对统计数据进行打假,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王东京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却把其中的奥秘给我们点了出来。他认为,我们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握有干部升迁大权的人处在金字塔的上层,干部要想进步,必须取悦上级,惟上是从。上面任用干部当然要看政绩。政绩怎么看?其实数字最有说服力。如果有人搞出一套考评标准,大而化之,笼统抽象而不能量化,让人不仅看不出纵向的变化,也难作横向比较,这样的考评标准,即使有也等于无。因此,考察干部听汇报、看数字,在现行体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
基层干部工作在下面,上面的大领导不能天天跟着,对真实的数字信息了解不充分,于是,这就使基层干部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虚报数字,易如反掌。同时,数字报得高,对上面的领导也有好处,两相权衡,上级领导也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放一马是一马。所以,就“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所以,王东京教授认为,如果不对现行的干部考核办法进行彻底改革,“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的游戏还会一直做下去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能看数字了呢?王东京认为当然不是。只要数字没有水分,真正反映政绩,出官就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数字由谁来出?如果由官来出,官员为了升迁,很难保证他不掺水分。如果改由民出数字,这样出来的数字就比较真实了。
让老百姓出数字,说白了就是要用“民意”测度政绩。并且政绩
的测度,既要看届中的表现,又要听一听“卸任回声”,如对任内的干部,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对新任的干部,到原来的单位“追评”一下,这些做法,都可以一试。也许有人会担心,那些工作泼辣,敢于得罪人的好干部,会不会因此吃亏呢?王东京认为,不会。他说,做好事得罪坏人,做坏事得罪好人,不做事的什么人也不得罪。经济学并不回避这种民主失灵的问题。但只要仔细分析,得罪坏人其实无关大雅,因为坏人毕竟是少数;再有,假如让选民明白,选举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又怎么会选那些无所作为的庸人呢?
三是对贪污腐败现象的解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干部队伍就象大浪淘沙,有的干部挺立潮头,引领风骚;有的则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对于后者,我们一般都是从其思想上去找原因。但做经济学分析,则更应该从体制上去找原因。王东京认为,存在决定意志,思想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在体制。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的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的制度,导出坏的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的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在这方面,西方人是比较务实的,他们认为,官员也是自私的,小到科员,大到部长,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能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会充分考虑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对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对企业,实行年薪制等。可我们的体制却是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的,毫不利己的公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就是低工资,大锅饭这一套。对干部的激励也是重精神,轻物质。王东京认为,物质激励不到位,是目前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王东京认为,一个人做不做官,自私的本性都不会改变。即使当上部长,也是如此。如果他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便极有可能以权谋私。从总体上看,古今中外,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按照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付出的劳动等于自乘的或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忽视物质激励,不仅不能使他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反而会诱使乃至逼迫他们犯经济错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员铁面无私,他处理腐败分子曾经用过“剥皮实草”之刑,但腐败却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官员的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难以支撑用度,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贫寒,怎能不催生腐败?近几年来,干部中出现的“59现象”,也值得我们反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中折射出的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这一点来看,对精兵简政和高薪养廉问题,应该合二为一,认真作些研究。
西方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西方国家搞的是“三权分立”,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样受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没有必要照搬,但对权力制衡这一套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学的。
这些年,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确实做了不少事,抓了不少人,也判了不少刑。但是如果对现行的监督体制作一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体制有不少的硬伤:一是错位。一是缺位。由于我们把官员认定为是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觉悟就越高,就越正确。所以我们的监督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什么权力也没有,却是被监督的对象;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这就是监督的错位。事实上,大官之中,贪污腐败的不乏其人,胡长清官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腐败起来,比一般人还要厉害。目前,我们的各级一把手至今仍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公检法都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怎么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我们是缺位的。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前几年,朱总理就提出过要看住国企的班子,有人对此议论纷纷,说朱总理不信任国企的干部。其实监督制度的设计是必须从“坏人”的假定出发的。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成好人,那还需要监督机制做什么?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监督多数人为多数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
监督权,腰杆子也就硬了,说话有人听了,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腐倡廉才能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夷陵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