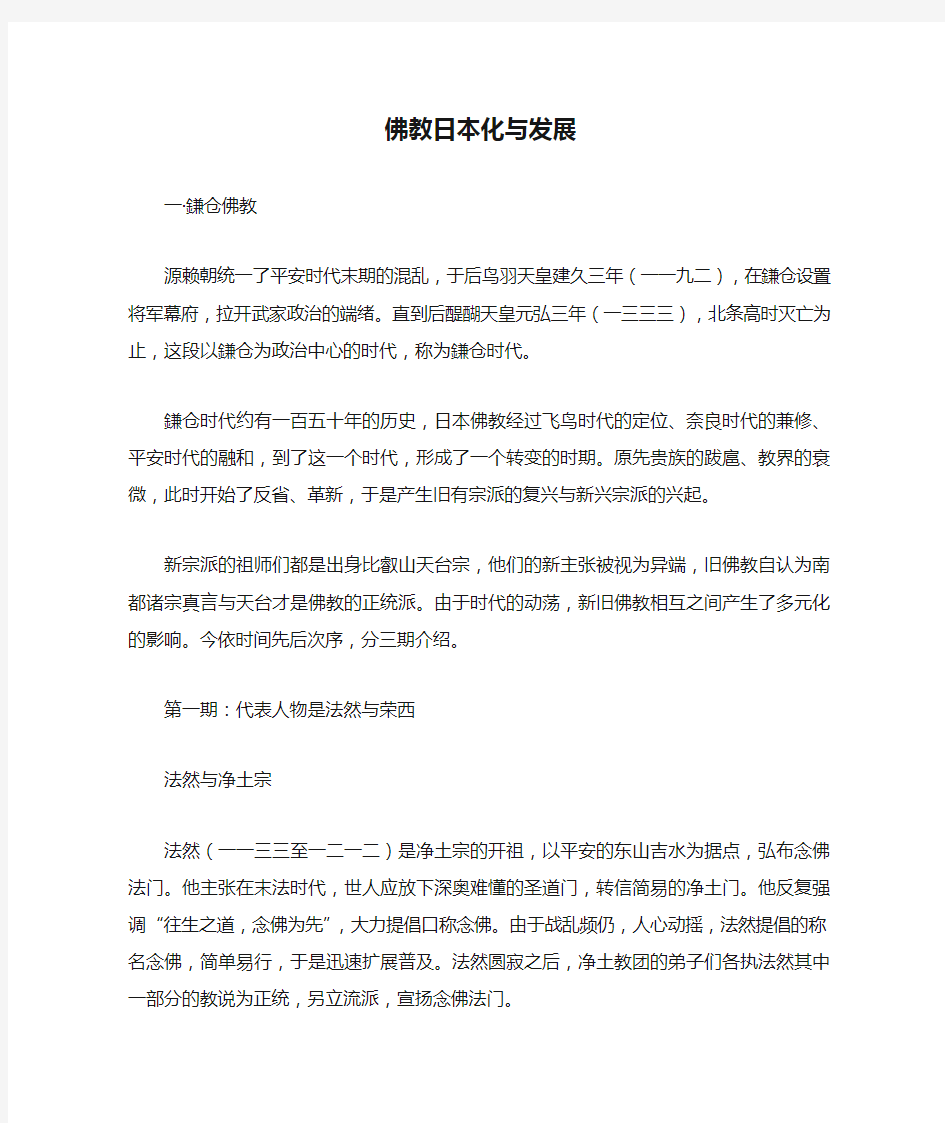

佛教日本化与发展
一·鎌仓佛教
源赖朝统一了平安时代末期的混乱,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仓设置将军幕府,拉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这段以鎌仓为政治中心的时代,称为鎌仓时代。
鎌仓时代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日本佛教经过飞鸟时代的定位、奈良时代的兼修、平安时代的融和,到了这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原先贵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时开始了反省、革新,于是产生旧有宗派的复兴与新兴宗派的兴起。
新宗派的祖师们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们的新主张被视为异端,旧佛教自认为南都诸宗真言与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统派。由于时代的动荡,新旧佛教相互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今依时间先后次序,分三期介绍。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与荣西
法然与净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是净土宗的开祖,以平安的东山吉水为据点,弘布念佛法门。他主张在末法时代,世人应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他反复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口称念佛。由于战乱频仍,人心动摇,法然提倡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之后,净土教团的弟子们各执法然其中一部分的教说为正统,另立流派,宣扬念佛法门。
荣西与临济禅
荣西(一一四一至一二一五)被尊为日本禅的开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余部;归国后,呈天台座主明云。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师事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他主张坐禅是万人之道,虽大钝少智之类,若能专心坐禅,必能得道;同时他也告诫弟子们,禅与天台、真言都是禅者应学之教。
荣西认为佛法与王法不可分离,兴禅可以护国,因而受到鎌仓幕府的信任,建立寿福寺,亦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
荣西之后,临济禅师辈出,加上宋朝诸位禅师的热心传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禅风,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与护持。
慈圆与贞庆
鎌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出身摄关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大力批评法然一派。又有兴福寺的贞庆,对于专修念佛的法然采取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持戒坚固,是弥勒净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亲鸾与道元
明惠与信满成就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了此书,惊讶他背离佛道,因此撰著《摧邪轮》严加批驳。
代表明惠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信满成就”,就是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书中并详述其修行次第。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至一二六二),又叫绰空,法然的弟子,是净土真宗的开祖。九岁时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烦恼中度日,离开比叡山后,皈依法然,主张绝对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亲鸾等七人也遭连坐之累,被流配边地,这就是日本净土史上
的“建永法难”。
亲鸾被流放五年后,获得赦免,便转往东国各地布教。东国地处偏远,既穷且无文化,如何让东国民众们体认弥陀的慈悲与大愿,是亲鸾净土思想的主要动力。他着有《教行信证》,阐述净土真宗的教义,强调以信心为本。他认为一念决定往生,这一念信得自弥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报弥陀恩的行为。晚年,他更主张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住于正定聚,与佛等同无异。比起法然的口称念佛,亲鸾的信心为本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
净土真宗强调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主张他力往生。亲鸾更自谓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种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
道元与曹洞宗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号希玄,二十三岁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访禅宗诸家,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归国后,在越前的山奥创建永平寺,成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然而道元的禅风并非只是承袭宋代禅风,他的本证妙修是本觉思想的开展。主张修证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实践法门的一句名言。
道元终生不喜接近权贵,虽有后嵯峨天皇御赐紫方袍,但终生不曾披搭,他认为禅者应在山林僻静处一心坐禅。遗有《正法眼藏》等诸多著作。示寂以后,弟子怀奘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鎌仓末期,到处天灾地变,饥馑瘟疫,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日莲与日莲宗
日莲(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二)出身渔民之家,一生惨遭法难的影响,却在一次次的流配当中,逐渐开展出他独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将《法华经》大分为前半的迹门与后半的本门二部。中国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迹门为重,日莲却以本门为终极。在他所著的《观心本尊钞》中说,观心是“观我己心,见十法界”,本尊则指久远成佛的释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张,观心(众生)与本尊(佛)本是一体;《法华经》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有藉著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才能证悟。日莲提倡口唱经题,并主张积极面对现实社会的奋斗精神,是日莲宗的一大特色。
一遍与时宗
一遍(一二三九至一二八九)所创净土宗的派别,称为时宗。宗名取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一遍礼净土宗西山派的圣达为师,致力称名念佛的修行。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要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死后就可往生。
一遍采取舞蹈念佛游行的方式传教,称为“踊跃念佛”。他带着写上“南无阿弥六十万人陀佛”的小纸牌,分送给他劝化的人,又主张修行人应舍弃一切世俗愿望,决定往生甚至经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称他为“舍圣”、“游行上人”。开始之时,他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至其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心在游行”。
鎌仓后期南都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学问佛教,也备受瞩目;弘扬戒律的俊,以泉涌寺为中心,提倡北京律,颇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与弟子忍性等在东大寺自誓受戒,并以西大寺为据点,兼倡戒律与密教,且积极发展慈善事业。
二·室町佛教
后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灭执权的北条高时,结束了鎌仓幕府。后来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占领鎌仓,后醍醐天皇于是往南迁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将军则
定都室町,这便是日本史上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代,称为室町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吉野室町时代的两百多年里,将军独裁,武士专横,全国人民痛苦不堪,尤其农民因税务负担繁重,生活困苦,纷纷起来反抗,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抗暴;领导参加抗暴的,有许多是净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莲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续鎌仓以来的教势,继续发展。由于战乱,佛教遂成为无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禅宗教系的发展
受到政局动乱的牵连,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响的便是禅宗。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很适合战乱中希求淡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时,只有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耀在社会各个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禅宗初传入日本时,就与当时的武士阶级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养方法;禅宗的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助长了禅宗信仰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有临济宗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
五山文学
延续着奈良、鎌仓时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为学问的中心,僧侣也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他们藉着汉文典籍作知识的传授,也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宁赴日,他的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南北朝时代,开创了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有七朝帝师之称的梦窗疏石(一二七五至一三五一)确立了五山文学的地位。所谓“五山文学”,是指由当时五山十刹的禅僧开展出来的文学风格。五山十刹的僧侣,一方面与幕府关系密切而备受保护,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进宋明的新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在汉诗方面,由推崇白乐天而改崇苏东坡与黄山谷,文体也由骈丽而转尊韩愈、柳宗元的古体。同时,还输入宋学与宋代的水墨画等。这些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创造了“五山文学”汉诗文、新儒学的研究及水墨画、书道等等高度的文化,这是日本汉文学中表现相当优秀的部分。
后来,藉着日本商船与元朝的贸易往来,中日两国的僧侣更进一步展开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对日本文学、书法、绘画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净土系诸宗的发展
净土宗在法然圆寂之后,分为多派,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净土真宗也是在亲鸾殁后分裂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莲如(一四一五至一四九九)中兴,以巧妙的说法,结合了已经分裂的诸派,甚至不少时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拥有许多农民信徒,并有强大的僧兵集团,在江户时代之后分为十派,而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时宗依然保持其独特的游行习惯,或在战场上与武士同行,称为阵军(或称从军僧),他们在江户时代被视为危险份子而饱受弹压。
日莲宗系的发展
日莲殁后,弟子间为了正统之争而相互对抗,日莲宗因此分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至一三四二)以京都为中心,热心布教,深受京都町众(工商业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谓“町众文化”的基盘。此外,由于现世利益追求的倾向越来越强,遂逐渐引入诸神信仰、咒术等。本宗也拥有强大的僧兵集团。
三·江户佛教
战国时代的动乱,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将秀吉的儿子秀赖杀灭,并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一六○○)在江户(今东京)
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称为江户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佛教采取压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毁寺院、没收寺产、掌握寺院经济等。到了德川家康,时局已渐趋稳定,他颁行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减少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纷争,而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户时代。在这时期,佛学和其他文化也在稳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续、进展。
德川家康是净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间,他一直站在保护佛教的立场,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响政治,因此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让宗派、寺院与僧侣都隶属于幕府的管辖。例如颁发所谓“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财务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对寺院的各种规定。此外,也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归属于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导致佛教的停滞与世俗化。到了江户末期,在儒学与国学的积极推展之下,“废佛毁释”的呼声高涨,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黄檗宗的开创
江户时代对外采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却有适度的开放,于是留居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这些华人为了精神需要,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长崎有名的有大唐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这时期由中国应邀前往日本的禅师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隐元隆琦(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隐元本属于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同于临济宗。他到日本之后,受到日本禅僧们的欢迎与幕府的重视,家纲将军并赐地为他建寺,隐元以他在中国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作为寺号,开创了黄檗宗。黄檗宗和临济宗、曹洞宗并称,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
为了奖励佛学研究,各宗纷纷举办所谓的学林、檀林等教育机构来研究佛学,只是因为江户幕府时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体系里,在一定的法规之下,佛学的研究、宗派的发展,大多延续上一个时代,而无特出的新表现。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稳定,学术研究风气兴盛,儒学、国学、文学、史学,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这时大放异彩,可说是日本文化史上最发达的时代。
试析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倾向表现与原因 发表时间:2018-06-19T14:17:26.687Z 来源:《素质教育》2018年7月总第276期作者:袁月[导读] 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深圳市龙城天成学校5181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形象“神气”十足,具有距离感与神秘感,但发展到唐朝太平天下,佛教形象则过于恬静温柔,少了几分“仙”味,多了几分人性。因而佛教造像慢慢走向世俗化倾向。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 唐朝是我国古代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其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可谓是古代史上一颗璀璨明珠,这其中就包括了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莫高窟的佛教造像,是根据时代背景下的真人形象塑造而来,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造像世俗化。何为世俗化?所谓世俗化,一是指形象本身似曾相识,与生活中人无异,“神性”几乎没有,甚至把菩萨做成妇女、仕女的形象;二是内容题材以西方极乐世界为题材成为主导,苦修苦练的题材不见。 本文主要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的造像世俗化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唐代时代的社会背景、百姓的总体风貌、佛教造像前后变化发展的特点和佛教造像对后世的影响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时期佛像造型的比较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帝王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寺庙,宣扬的内容是忍辱、苦修和自我牺牲。造像鲜有明显的个性,他们姿势呆板、容颜冷静、服饰单一,佛像周围的顶光、佛座、法宝一样不缺,有十足的“神味”,此时的佛像显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到了唐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昌盛,全国上下呈现一片祥和平安的气象。这时内容以表现西方极乐世界、宣扬民间欢乐和幸福生活为主题。菩萨的造像富有了感情色彩,面容娇媚、服饰时尚,俨然一位美丽的唐朝妇女形象,打破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赋予了佛像现实、亲近的特点。 二、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具体表现 1.题材世俗化。唐朝,故事选题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苦修、忍让、自我牺牲等题材逐渐消失,出现了许多关于现实生活、表达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的题材内容。甚至连“张骞通西域”这样世俗化内容的题材都出现在了壁画造像中。 2.菩萨观音造型世俗化。魏晋时期《法华经普门品》有明确的“善男子”的记载,《华严经》中也说“勇猛丈夫观自在”,说明观音菩萨本来是男性。自从唐朝之后造型就逐渐女性化,原因之一是与道教崇尚女性的观念有直接联系,道教认为天地万物源于母体,它化育天地万物而生生不息,故“可以为天下之母”,唐代菩萨造像在受到道教的这种观念影响,具有很明显的女性特征。 3.供养人形象世俗化。供养人,指的是在修建寺庙或是宗教活动中,提供过人力物力的虔诚教徒。中晚唐时期,供养人的形象和真人大小一般,衣服多是当时流行的装束,描绘的许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三、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繁荣。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黄金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并不像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魏晋时期的人民那么期渴望神灵眷顾。佛教造像形象都是按照盛唐妇女的时尚打扮造像。侧面反映了唐人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与享乐主义情怀。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特色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经济因素是唐造像世俗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2.市民阶层的壮大。唐朝时期是中国人口一个新的复苏时期,人口总数猛增到5000万人,仅城镇人口就有2500多万。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城镇人口不断扩充,市民阶级也不断壮大。从唐朝文学、诗歌、小说均向百姓化过渡,绘画、篆刻更是具有强烈世俗化审美情趣,都是一些表现人民生活的民俗题材。 3.佛教政教功能的退化。魏晋时期的社会乱战频繁,佛教是给民众带来虚幻的精神安慰剂,这样的政教功能十分必要。而唐朝的老百姓不像以前单纯去圣朝,佛教原本的教化功能逐步走向衰落,这也是促使佛教造像渐渐走向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影响 造像随各朝历史变化而变化。到唐朝时期塑造了日后十分经典的菩萨形象,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菩萨造像,大都是在唐造型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都有着唐朝时期情切柔情丰腴的韵味。可想而知唐朝莫高窟造像对后世佛教造像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最初的出现是为了在乱世之中稳定民心,给生活境地悲惨的人民带来一丝光明的慰藉。而唐代莫高窟佛教造像艺术巧妙地突破了佛教的宗教教义,打破了魏晋时期的“神性”,创造了世俗化、女性化的特色。这说明任何艺术特点都是在当时特定时期背景下呈现的。受着当时政治经济、时代背景的影响,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神”在当时社会时代也必然带有世俗的气息。参考文献 [1]张育英《中国佛道艺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2]李福顺《中国美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4]陈绶祥《唐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 的吸收
浅谈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摘要】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它对外来文化很少排斥,而是积极地消化、吸收,并且其对外来文化并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国情与民情的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最后使其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开放的社会和日本人的一些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应该说,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日本外来文化吸收创新原因中国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民族,每当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够为适应自身的要求,有目的地、系统而又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融合、创新,最终形成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偏居东亚的岛国,四面环海,可谓“远东孤儿”,见闻闭塞,对外来文化素来具有新鲜感,因此有人说:“从特定意义上讲,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1】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也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一、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 从日本文化史来看,日本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接受外来文化有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是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第二次是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欧文化。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吸收了美国文化。【2】 早在2000多年前,中日两国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友好往来,所以在中国的隋朝、日本的推古朝以前,中日就出现了交流。在日本绳文时代末期,为了躲避战乱等,很多的中国人经朝鲜半岛移民到日本,同时也将先进的文明与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到了日本,比如说水稻、铁器、青铜器等,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公元五六世纪以后,日本更加积极地吸收中国的文化,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吸收,还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这个时候日本正是推古朝,圣德太子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教文化,在日本进行了推古朝的改革,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制定“宪法十七条”,都是引用中国典籍,使用了儒、法、道、佛教的一些规范和思想概念。而且为了更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他还主动派出遣隋使到中国去,这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动力,推到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公元618年,隋亡唐兴。当时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变化发展的时期,为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和引进唐朝制度,日本朝廷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而这个时期遣唐使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派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中古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个时候也是日本“百事皆仿唐制”的“全盘唐化”的时代,是“唐风”文化盛行的时代。日本学者坂本太郎指出:“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无不与唐风有关。人们认为唐文化具有最高的水平,尽早达到它那样的水平,是当时一般的共同目标。”【3】 当然,日本在吸收、移植中国文化是,还是注意了日本的国情的,是有所变通的。比如说,唐朝的尚书省中除六部外还有九卿,这是沿王制而来的。九卿当中又有大理寺这样的司法官,但刑部也有司法官。于是,与司法有关的官职就产生了重复。另外,尚书省六部之一的工部,与将作监并存,户部与内务大藏并存,礼部与礼仪使并存等等,这样重复的官
圣严法师《佛教对宇宙生命的来源及看法》 护眼色:绿橙棕黑字体:粗体大中小作者:圣严法师发布时间:2010-6-14 22:20:45繁體版 佛教既然不相信另有一个宇宙的创造神,但是宇宙的存在,不容怀疑,生命的存在,也不容否定。 佛教相信:宇宙的原素是永恒的,生命的因素也是永恒的,前者是物质不灭,后者是精神不灭。所谓永恒,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本来如此,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实际情况。 佛教相信:宇宙形态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那是由于众生所造的“业力”的结果。 业力是指有情众生(动物)使每一桩或善或恶的行为,像各种的颜色一样,继续不断地熏染到生命的主体——识田中去,再从识田之中,等待外缘的诱导而萌芽生长,正像播种在泥土中,等待日光、空气、水的诱导而萌芽生长,这在佛教称为业力的现行。业的造作是业力现行的因,业力的现行,是业所造作的果,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说明这个意思。 业,有个人单独造作的,也有与他人共同造作的;有的虽然单独造作,但也可以和他人相同,有的虽与他人共同造作,但也各有轻重不同。因此,业的种类,从大体上说,分有“共业”及“不共业”两大类。 由于共业,所以感得同样的果报;地球,便是由于地球世界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数众生的共业所感,而有各类不同的共业,所以也感得各种不同的世界,太空之中,宇宙之间,有着无量无数的世界,它们的成因,都是由于各类不同的无数众生,所造各类不同的共业而成。所以,火星上如果真的有人,火星人的形体,未必也和地球人的形体一样。至于那些无人的星球,乃至那些没有生物存在的星球,虽不是众生活动的舞台,但却也是为了众生活动的舞台而存在;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种现象没有其存在的理由。比如,太阳上不可能有生物,但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的生物也将无法生存;虽然尚有许多的事物,无法用科学的观点证明其存在的理由,但在佛教的解释,一切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那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摘要:公元前 5 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 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
中国佛教现状 编者按Editor's notes加拿大时间2017年6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多伦多湛山精舍承办、多伦多大学协办的中加美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隆重开幕。论坛主题为“圆融中道,持久和平”,来自中、加、美三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及加拿大联邦、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有关政要、有关社团、各界嘉宾和多伦多大学部分师生、佛教护法居士数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多伦多大学作题为《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的专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以下为学诚会长专题讲座发言全文: 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VenerableMaster Xuecheng,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One:Chinese Buddhism: Past and Present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Tod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present h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hievemen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have a true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vigorous Chinese Buddhism. 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对于不是很了解中国佛教的人来说,很容易用两种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佛教:一是停留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而将中国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甚至脱离现实的存在;二是完全站在现代时空因缘下、以实用角度看待中国佛教,忽视其穿越两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两种视角的片面和局限性,往往导致对中国佛教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佛教抽离于时代,认为佛教是落后的乃至反现代的;二是将佛教抽离于历史,使之肤浅化、世俗化。First of all, I want to put the 21st-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because its present situation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long progress. It comes from the past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acts asan isolated fragment.To those who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Buddhism, they tend to treat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with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阅读《日本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有感 发表时间:2019-04-22T15:05:07.18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2期作者:李欣然董彦灵[导读]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国际关系学院,100089)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圣德太子是佛教在日本得以传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用政府法令的形式,在治上提倡普度济世,文化上鼓励人们为为国家众生献身,他对佛教教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将佛教与日本的民族精神实现了最初的融合。自圣德太子开始至以后的几个年代,日本的佛教思想大抵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政治上,保卫国家,二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救世济人的大乘佛教的思想。佛教之所以能在日本得以发展,一是要和日本的政治意识相互适应,其次它也要和日本的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其中包括日本的神道教和祖先崇拜。由于镇护国家的主张,佛教先是得到了社会统治着的青睐,再加上与日本本土信仰的融合,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镰仓时代,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日本佛教已经基本形成。代表性的宗派有,净土真宗,日莲宗,禅宗。净土真宗相比以往佛教流派主张个人佛教,在家佛教,以绝对他力的信仰作为基点,将出世的佛教与世俗生活融合在在一起,以佛教为基本信念,肯定人间生活的主体性。该教派从表面上来是将自己融入佛家慈悲之心中,绝对他力的宗教性格,立足点却在个人的觉悟。同时追求这种觉悟的并不只是僧侣,而是芸芸众生,该教派对人间人生生命的肯定,被称为日本佛教史上宗教感情最高顶点。日莲和尚主张即身成佛,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实社会的改造方面,他想用教义改变社会现实,将人间变成佛间净土。同时日莲主张用超教宗的政治力量消灭自己的敌人,这其实是日本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独立的一个重要特征。日莲教对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格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日莲教也是当今日本信仰人数最多的佛教流派。禅宗则是更重视修行过程的一个教派,根据道元的说法,每个人的生活历程及其过程即是其目的和意义。人生的每一刻都可以寻找到真谛,不需要到处寻找人生的真理。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道元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被后代人称为日本理性的顶点。 日本文化精神的中枢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这是日本文化的源泉。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受制于天皇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佛教的祖师崇拜。人民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亦使民族意识通过祖师崇拜得以强化。同时日本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形成了多重信仰的现状。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应该放在日本教这个大范围内加以研究。 首先,我对这篇文章最感兴趣的几点是日本人将自然作为人间社会的立足点并从中产生了绝对的精神秩序,神化自然概念,以自己为中心,以绝对信仰为基础,同时他们会神化甚至圣化民族精神。我觉得这在二战期间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对完满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民族追求精神和意志的极限,比如在侵华系列的影视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的,如果日本军人某一次任务执行失败,他们则会选择切腹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绝对的神化的民族精神也使得日本的集体主义十分盛行,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日本人对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成了一种集团意识,并在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他们对集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同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我觉得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信仰有这重要的联系。武士道吸纳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死生如一”和神道主义的天皇信仰而产生,受原始信仰和崇拜的影响,成为日本民族一个较深层的文化心理,曾主导着这一民族的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对其发展影响较为深远。但是在二战期间,武士道开始沦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在此精神的影响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入侵的不归路。 以上则是我对该篇文章的总结概括以及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11.16.19
“菩提心”与“忠义心” ———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余秉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安徽 合肥 230053) 摘 要:作者通过赴九华山进行考察,并且研读有关学术资料,提出如下见解:九华山佛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九华山佛教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世俗化,表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九华山高僧宗杲禅师“忠君爱国” 思想的分析,从宗教理论的角度,探讨九华山佛教对于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贡献。 关键词:九华山佛教;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宗杲;儒释调和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1-0013-02 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在赴九华山考察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九华山佛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这一特点。而九华山佛教文化之所以历久不衰,佛事活动之所以长期兴旺,也正由于它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特点。本文试图从宗教理论方面,就九华山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作一考察。 从宗教理论看,宋代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这一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 所谓“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了佛家的最高智慧。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佛教义理,“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这正是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便不曾停止。他们批判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无君无父”、“泯灭人伦”。例如程颢就曾说过,佛家“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①这正是对不承认世俗社会纲常伦理的佛门教义的抨击。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俗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俗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出现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②的说法,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而作为九华山高僧之一的宗杲,则更进一步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这对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从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12岁出家。《大明高僧传》称其“灵根夙具,慧性生知”。17岁落发受戒后,曾参拜 13 ① ②《圆悟佛果禅师语录》。 《二程遗书》,卷二。
浅谈日本民族性格 APEC期间,中日首脑终于跨出了打破僵局的历史性一步,习主席和安培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个信息无疑是积极的信号。这却是一个“尴尬”(awkward)的握手。从合照中,中国人民的原谅是有限的,有着强烈的不满。历史以来,我们常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来形容日本这个邻邦。我们每个人也都会这样的两句日语:“沙扬娜拉”“八格牙路”。我们更每天都在无形之中接受着日本的各种影响,从汽车、电视、空调等硬件到动漫、影视、饮食等文化软件。然而,即使我们使用他们的产品、感受他们的文化,日本民族于我们又是那样的陌生和遥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日本所知甚少。这确实是让我们震惊和可怕之处! 我们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几乎只停留在一百多年前地中日海战之后,这一百多年地历史,深深地震惊着国人。无论是从不起眼的小国迅速发展为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在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中先后将两个庞然大物的国家放倒,更无论在二战中倒下的日本仅在二十多年后就再度崛起。这一切给我们太深刻地印象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国家? 本尼迪克曾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罪捉摸不透的。”李光耀也直接地指出:“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确实,日本是我们绝对一言难尽的国家,他有我们太多的怀疑和不解。历史上日本曾极大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朝,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属国,已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引入到本国。因此,日本民族的特性之中是有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民族的影子的。首先的共同点就是思维方式。中国和日本人都偏向于形象思维和直觉的感悟。这一点从中日在对山水、画、茶道等方面追求简约、淡远的取向可以看出。而中日两国人民都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虽然在日本是所谓的“神道教”但其实质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其次,是内敛。中国人是不喜欢出头的,在日本也是如此。讲究含蓄忍让是共同的为人处世哲学。这样的含蓄在日本称为“腹艺”。第三个共性则是集体主义。日本有一句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这与中国的“枪打出头鸟”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一样的。由此产生的是辈分严格的尊卑。儒家文化在此的强大影响不言而喻。这便形成一种压抑个性的性格。
2010年1月中州学刊Jan.,2010第1期(总第175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历史研究】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吴春燕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 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70—03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 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吴春燕,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 071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111
浅析中日古典园林的异同点 以苏州的沧浪亭和龙安寺方丈庭园为例 摘要:中日古典园林和日本古典园林均为东方两颗璀璨的明珠,他们都崇尚自然之美,意境之美。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文精神上的不同导致两国园林各有千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苏州四大名园之首的沧浪亭和日本龙安寺庭园庭院,剖析中日两国在造园手法,造园思想,创意布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便我们更好学习和利用造景的技巧,继承古代造园师智慧。 关键词:中国园林日本园林异同点沧浪亭龙安寺方丈庭院 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景观领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景观一词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然而随着各种景观形式的出现,作为原始的、代表劳动人们智慧的古典园林,却逐渐被人们遗忘。尤其在中国,古典园林曾经在世界园林史上独领风骚,备受关注。能代表中国古典园林辉煌成就的当属苏州四大园林。中国与日本一水相隔,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在园林领域,日本园林在很多方面也师从中国。日本园林中具有代表的枯山水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上存在很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早的园林景观,最古老的园林景观,位于苏州市城南。沧浪亭最初为北宋诗人苏舜钦官场是失意后所作。后屡易其主,清同治重建,遂成现状。“沧浪胜迹”坊耸立西部水岸边,坊测沿池北岸,种植碧桃垂柳,树荫下石凳成排,可供游人观景。沧浪亭虽不能成为中国园林的唯一最美,却也可以称得上最美之一,能够很好的成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 龙安寺方丈庭院和大德寺大仙院庭院是日本枯山水的双壁。龙安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其方丈庭院建于1499年,设计者是相阿弥。方丈庭院是以极度抽象的构图,最简洁的材料——15块石头、满庭的细沙及低矮的围墙勾画出一幅苍凉孤寂、象征万顷海洋的永恒图景。东西长25m,南北宽11m。历来对此院的解释是见仁见智。 图1 沧浪亭平面图
中国目前有四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其中以佛教为首.佛教无论从历史影响力,还是于中国文化,中国国民地关系上,都远非其他教派可与之比拟地.可以说佛家文化已经早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地长河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地一部分.本篇文章通过回顾佛教在中国地发展历程,探讨宗教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对佛教这一东方大教有一个更深跟全面认识地目地. ,佛法东传,白马西来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五到六世纪,起源地在今尼泊尔,创始人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后在中国流传,所谓佛法东传,白马西来.关于中国佛教起源地说法有多种,其中比较古老而最富盛名者,当推汉明帝地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书地记录:初,明帝遇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笔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地起源.汉明帝十年,有印度僧人用白马驮着经书到达洛阳,在明帝地首肯下,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而当时兴建地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寺地雏形.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应该是一个渐进地过程,可能早在秦始皇时代,借着往来于西域地商人,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一些佛教地事物,至于中国人开始信仰佛教,应该是从后汉时代开始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时间进入到三国时期,在此期间内,佛教取得了进一步地发展,尤其是北方地魏国和南方地吴国.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说魏国佛教是汉代佛教地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地僧人来华,从事佛经地翻译工作.这些带着信仰,不远万里来华弘法地僧人大都收到了当时统治者地欢迎与支持.上层对佛教事业地肯,定必然会带动民间佛教地发展.在魏朝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本土僧人——朱士行,他也是第一个到西域取经地汉人,作为求佛地先行者,他比玄奘大师早了约四百年,只可惜后来客死西域.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汉末到三国这段时期,从中国佛教地发展来看,尚属启蒙阶段,佛教活动主要围绕译经展开,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地佛教体系.但是,经过这数十年地发展,佛教典籍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佛教地主旨经意也开始逐渐扩散传播,为以后佛事活动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一个宗教在一个地区地发展总需要一定地社会基础.佛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一定地气候首先得益于统治者地欢迎与扶持,东汉某年,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满情绪加深.这使统治者有了危机意识,希望能通过某种手段巩固自己地统治.而佛教恰在此时出现了,佛家教义讲究忍受现世,强调因果轮回,一个忍字深深打动了统治者,他们希望自己地百姓都能忍现世之苦,以此减少反抗因素.于是,一场宗教与政治地合作开始了.再者,佛教能在当时打入社会内部,还要得益于中国思想地半真空,当时一度被扶为正统地儒家思想已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人们兴起出世地愿望,因此,佛教能“趁虚而入”.在这时,佛学起到地是思想工具,思想寄托地作用,因为当时佛学地不成熟,在民众地心目中其还没有上升到宗教信仰地高度.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严格意义上讲,此时地佛教仍是天竺西域地佛教,而非中国自己地佛教.佛教在中国地本土化之路,仍前路漫漫.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神通类”高僧——佛图澄 西晋时地佛教活动仍以已经为主,其中最杰出地译经师是竺法护.他长居敦煌,并随师周游西域,通晓三十六种西域语言,他共译出一百五十多部三百多部经典.对佛教地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地十六国统辖.这些北方地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用佛教来巩固他们地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地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地发展.其中后赵地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