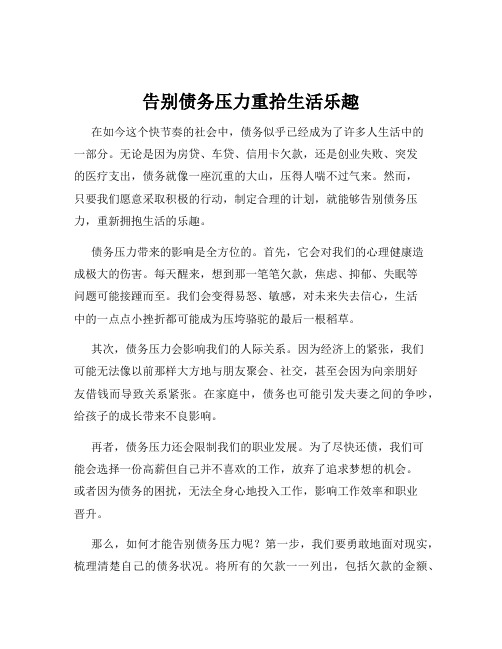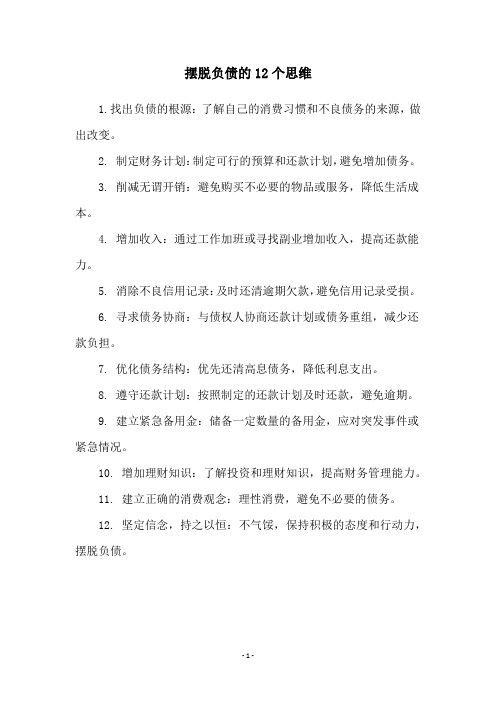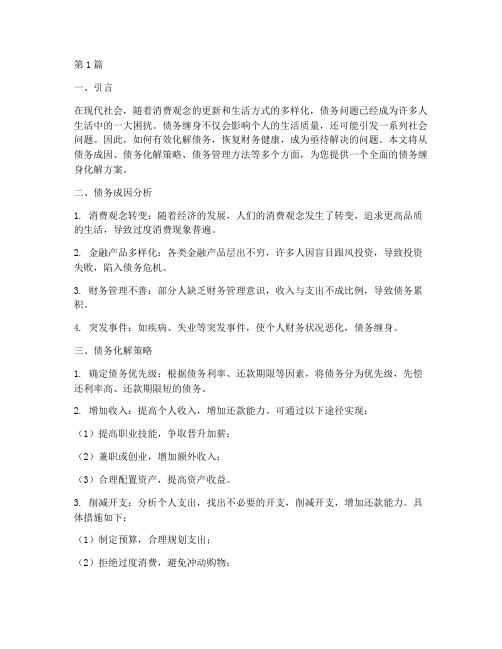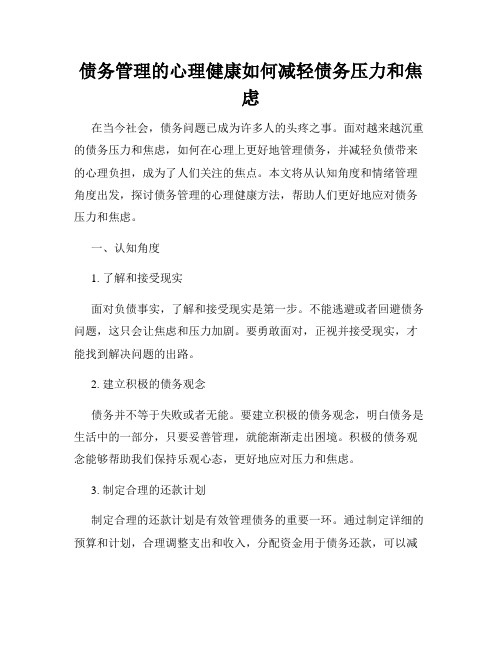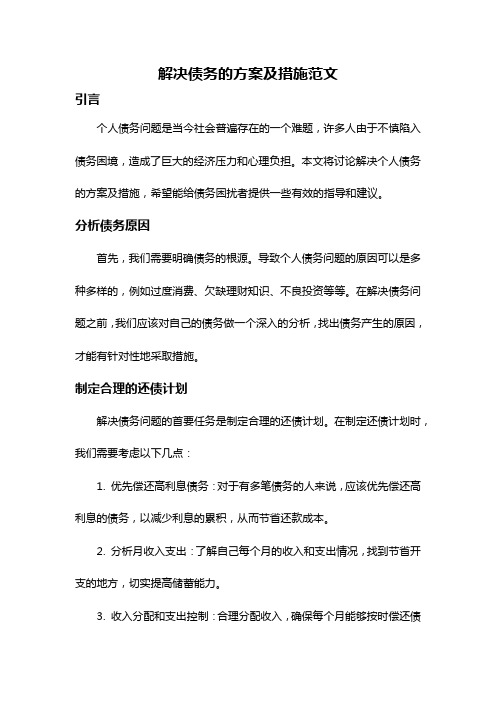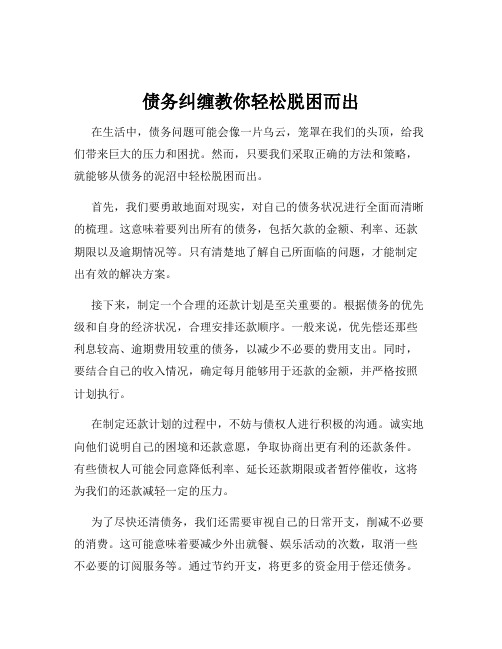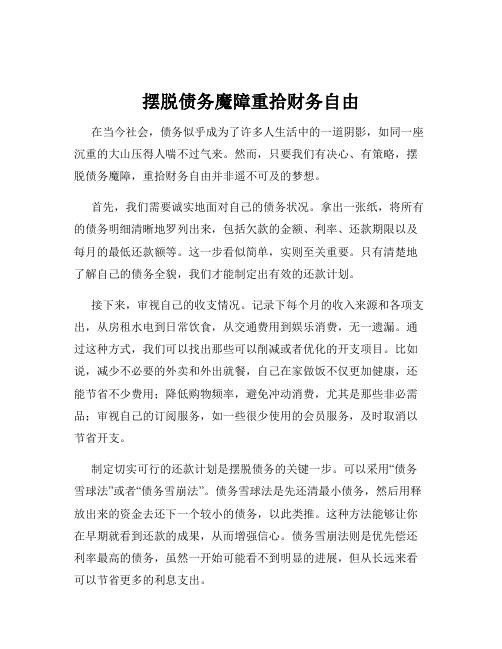“我在香港,25号回去就把钱打给你”。1月20日,吴小姐这样回复我,是在谈该支付给我的货款。去年底赶出这批货后,我一直没有收到钱。工人要回家过年,我只好先四处借钱把工资和奖金结算了,年前还要把老李的钱还了。欠债不过年,这是中国人的古训。
25日,没有动静。26日,我只好再去催:“我是借钱发的工资,你教我怎么办?”吴小姐反呛道:“我收不到款,哪来钱给你?上回那批货现在还没出完呢……客户要求套装配上裙子,才好卖。你还得做,出了货才有钱给你。”我和吴小姐几乎吵起来:“你那个收货的小妹,瞒着你,吃掉了我50套,跑了,又怎么说?”气呼呼的我挂掉了电话。
欠薪和不断扩大的债务逼着我困兽犹斗,大单我是不敢接了,在做了几批小单后,职业的敏感让我意识到大环境已不允许我再做了。2008年4月,我决定关闭工厂。此后,东莞迅速蔓延开来的倒闭潮,真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清算和私下里的变卖已在进行了。债务是如此无法面对,我变卖了我的房产,又向亲友借了一笔钱,结清债务的我,真的是一贫如洗。
“这批货客户不要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王女士打完这声招呼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2007年8月份的事情。当时,我看着那批价值30万元的压仓货,有说不出的窝囊。祸不单行,到12月份,拿走了价值40乱了手脚。春节欠薪也发生了,2008年的春节真是忐忑不安,订单突减,市场萎缩得非常快,先是欧美大客户迟迟不肯下单;跟着,就是我最大的客户取消了每年40万件毛衣的订购计划。
我与吴小姐已经有近10年的生意交往了。两年前,升了职的公务员丈夫另觅新欢后,她独自抚养11岁的女儿。一个女人在生意场上打拼,的确也不容易。她要是手头宽裕,也不至于如此。再一次被债务困扰的我,头又痛起来了。
2000年初,移居加拿大的港商跑掉我45万元货款后,我的生意就垮了。加上在赌场上输掉10万元的丈夫的打击,我几乎一蹶不振。2001年,只得在一家机关找份编外文员的工作,聊以糊口。一年后,作了老板的吴小姐,给了我一批手工外包活,由此,我开始承接多家工厂的手工外包订单。利润虽然不到10%,但由于外单不绝,还是能找到大把干活的人。到2006年,我花掉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30万元,盘下了一家没注册的毛织厂,加上借来的15万元和合伙人的30万元投资,周转了我的生产线。
纷至沓来的外贸订单和大量闲散务工人员,催生了我这类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都“冒险”经营,为40%-50%的工人办暂住证,可以躲进地头上的保护伞。一顿饭,再加上两三千元的红包就能逃税。为了与同行竞争,由货款不足就开工,发展成了先出货、后收款的近乎自杀式的经营方式。
35岁的金先生,来自韩国,独自在市区租了一间办公室。间或为20余家服饰厂下订单,然后销往国外。而年近40岁的王女士,则把我这里的毛织品销往北方和俄罗斯。头一年,还算过得去,我差不多有了40万的盈利。然而,接踵而来的一切却完全打破了常规。
城中村的简陋租所、一间拥有30来名散工的作坊,就是我的现在。吴小姐变成了我的客户,我依然面临烦人的债务。如今,我每每走入这个繁荣从未间断的国家,常常沉入一种莫名的迷惘──这一切“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