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的婉约词特点
- 格式:doc
- 大小:76.50 KB
- 文档页数: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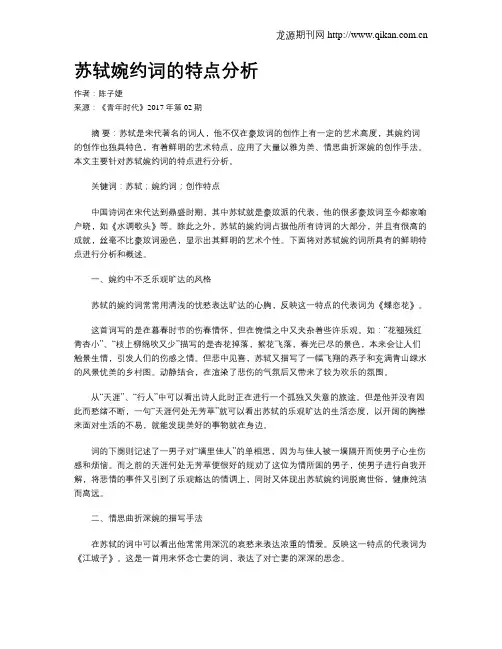
苏轼婉约词的特点分析作者:陈子婕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02期摘要:苏轼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他不仅在豪放词的创作上有一定的艺术高度,其婉约词的创作也独具特色,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应用了大量以雅为美、情思曲折深婉的创作手法。
本文主要针对苏轼婉约词的特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创作特点中国诗词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其中苏轼就是豪放派的代表,他的很多豪放词至今都家喻户晓,如《水调歌头》等。
除此之外,苏轼的婉约词占据他所有诗词的大部分,并且有很高的成就,丝毫不比豪放词逊色,显示出其鲜明的艺术个性。
下面将对苏轼婉约词所具有的鲜明特点进行分析和概述。
一、婉约中不乏乐观旷达的风格苏轼的婉约词常常用清浅的忧愁表达旷达的心胸,反映这一特点的代表词为《蝶恋花》。
这首词写的是在暮春时节的伤春情怀,但在惋惜之中又夹杂着些许乐观。
如:“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描写的是杏花掉落,絮花飞落,春光已尽的景色,本来会让人们触景生情,引发人们的伤感之情。
但悲中见喜,苏轼又描写了一幅飞翔的燕子和充满青山绿水的风景优美的乡村图。
动静结合,在渲染了悲伤的气氛后又带来了较为欢乐的氛围。
从“天涯”、“行人”中可以看出诗人此时正在进行一个孤独又失意的旅途。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愁绪不断,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就可以看出苏轼的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以开阔的胸襟来面对生活的不易,就能发现美好的事物就在身边。
词的下阕则记述了一男子对“墙里佳人”的单相思,因为与佳人被一墙隔开而使男子心生伤感和烦恼。
而之前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便很好的规劝了这位为情所困的男子,使男子进行自我开解,将悲情的事件又引到了乐观豁达的情调上,同时又体现出苏轼婉约词脱离世俗,健康纯洁而高远。
二、情思曲折深婉的描写手法在苏轼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常常用深沉的哀愁来表达浓重的情爱。
反映这一特点的代表词为《江城子》。
这是一首用来怀念亡妻的词,表达了对亡妻的深深的思念。
词的开头“十年生死两茫茫”表达了苏轼在这十年中与妻子阴阳两隔的孤寂心境,并有“不思量,自难忘”的直抒胸臆,表现出对亡妻刻骨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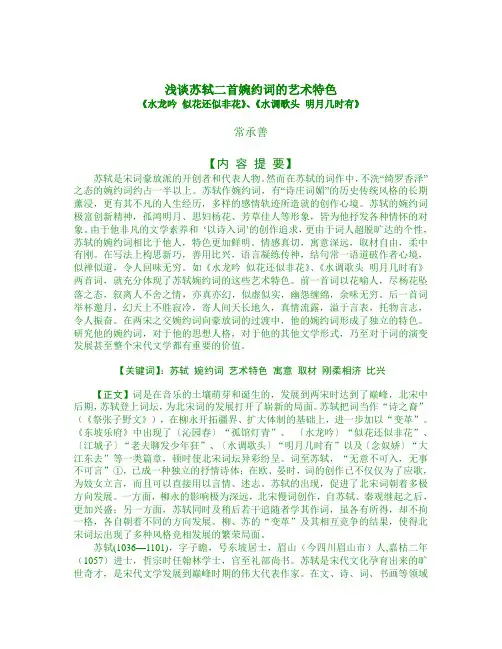
浅谈苏轼二首婉约词的艺术特色《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常承善【内容提要】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
然而在苏轼的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态的婉约词约占一半以上。
苏轼作婉约词,有“诗庄词媚”的历史传统风格的长期薰浸,更有其不凡的人生经历,多样的感情轨迹所造就的创作心境。
苏轼的婉约词极富创新精神,孤鸿明月、思妇杨花、芳草佳人等形象,皆为他抒发各种情怀的对象。
由于他非凡的文学素养和…以诗入词‟的创作追求,更由于词人超脱旷达的个性,苏轼的婉约词相比于他人,特色更加鲜明。
情感真切,寓意深远,取材自由,柔中有刚。
在写法上构思新巧,善用比兴,语言凝练传神,结句常一语道破作者心境,似禅似道,令人回味无穷。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两首词,就充分体现了苏轼婉约词的这些艺术特色。
前一首词以花喻人,尽杨花坠落之态,叙离人不舍之情,亦真亦幻,似虚似实,幽怨缠绵,余味无穷。
后一首词举杯邀月,幻天上不胜寂冷,寄人间天长地久,真情流露,溢于言表,托物言志,令人振奋。
在两宋之交婉约词向豪放词的过渡中,他的婉约词形成了独立的特色。
研究他的婉约词,对于他的思想人格,对于他的其他文学形式,乃至对于词的演变发展甚至整个宋代文学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艺术特色寓意取材刚柔相济比兴【正文】词是在音乐的土壤萌芽和诞生的,发展到两宋时达到了巅峰,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
《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顿时使北宋词坛异彩纷呈。
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①,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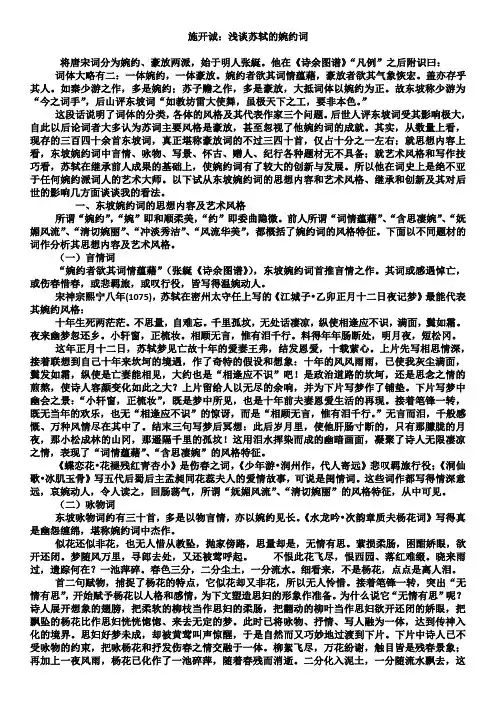
施开诚:浅谈苏轼的婉约词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人张綖。
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
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盖亦存乎其人。
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赡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段话说明了词体的分类,各体的风格及其代表作家三个问题。
后世人评东坡词受其影响极大,自此以后论词者大多认为苏词主要风格是豪放,甚至忽视了他婉约词的成就。
其实,从数量上看,现存的三百四十余首东坡词,真正堪称豪放词的不过三四十首,仅占十分之一左右;就思想内容上看,东坡婉约词中言情、咏物、写景、怀古、赠人、纪行各种题材无不具备;就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看,苏轼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使婉约词有了较大的创新与发展。
所以他在词史上是绝不亚于任何婉约派词人的艺术大师。
以下试从东坡婉约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继承和创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东坡婉约词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所谓“婉约”,“婉”即和顺柔美,“约”即委曲隐微。
前人所谓“词情蕴藉”、“含思凄婉”、“妩媚风流”、“清切婉丽”、“冲淡秀洁”、“风流华美”,都概括了婉约词的风格特征。
下面以不同题材的词作分析其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
(一)言情词“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张綖《诗余图谱》),东坡婉约词首推言情之作。
其词或感遇悼亡,或伤春惜春,或悲羁旅,或叹行役,皆写得温婉动人。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写的《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最能代表其婉约风格: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年正月十二日,苏轼梦见亡故十年的爱妻王弗,结发恩爱,十载萦心。
上片先写相思情深,接着联想到自己十年来坎坷的境遇,作了奇特的假设和想象: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我灰尘满面,鬓发如霜,纵使是亡妻能相见,大约也是“相逢应不识”吧!是政治道路的坎坷,还是思念之情的煎熬,使诗人容颜变化如此之大?上片留给人以无尽的余响,并为下片写梦作了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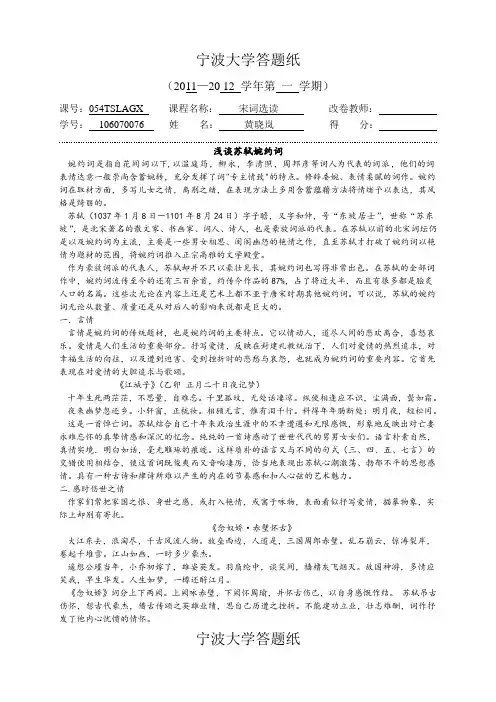
宁波大学答题纸(2011—20 12 学年第一学期)课号:054TSLAGX 课程名称:宋词选读改卷教师:学号:106070076 姓名:黄晓岚得分:浅谈苏轼婉约词婉约词是指自花间词以下,以温庭筠,柳永,李清照,周邦彦等词人为代表的词派,他们的词表情达意一般崇尚含蓄婉转,充分发挥了词"专主情致"的特点。
修辞委婉、表情柔腻的词作。
婉约词在取材方面,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绪,在表现方法上多用含蓄蕴藉方法将情绪予以表达,其风格是绮丽的。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也是豪放词派的代表。
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
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人,苏轼却并不只以豪壮见长,其婉约词也写得非常出色。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流传至今的还有三百余首,约传今作品的87%,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对后人的影响来说都是巨大的。
一.言情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
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爱情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
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
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一首悼亡词。
苏轼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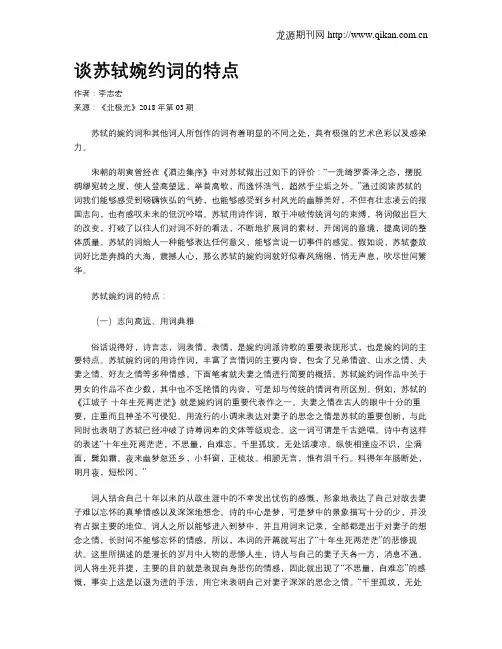
谈苏轼婉约词的特点作者:李志宏来源:《北极光》2018年第03期苏轼的婉约词和其他词人所创作的词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具有极强的艺术色彩以及感染力。
宋朝的胡寅曾经在《酒边集序》中对苏轼做出过如下的评价:“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通过阅读苏轼的词我们能够感受到磅礴恢弘的气势,也能够感受到乡村风光的幽静美好,不但有壮志凌云的报国志向,也有感叹未来的低沉吟唱。
苏轼用诗作词,敢于冲破传统词句的束缚,将词做出巨大的改变,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词不好的看法,不断地扩展词的素材,开阔词的意境,提高词的整体质量。
苏轼的词给人一种能够表达任何意义,能够言说一切事件的感觉。
假如说,苏轼豪放词好比是奔腾的大海,震撼人心,那么苏轼的婉约词就好似春风绵绵,悄无声息,吹尽世间繁华。
苏轼婉约词的特点:(一)志向高远、用词典雅俗话说得好,诗言志,词表情。
表情,是婉约词派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
苏轼婉约词的用诗作词,丰富了言情词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兄弟情谊、山水之情、夫妻之情、好友之情等多种情感。
下面笔者就夫妻之情进行简要的概括。
苏轼婉约词作品中关于男女的作品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艳情的内容,可是却与传统的情词有所区别。
例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婉约词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夫妻之情在古人的眼中十分的重要,庄重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用流行的小调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是苏轼的重要创新,与此同时也表明了苏轼已经冲破了诗尊词卑的文体等级观念。
这一词可谓是千古绝唱。
诗中有这样的表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人结合自己十年以来的从政生涯中的不幸发出忧伤的感慨,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去妻子难以忘怀的真挚情感以及深深地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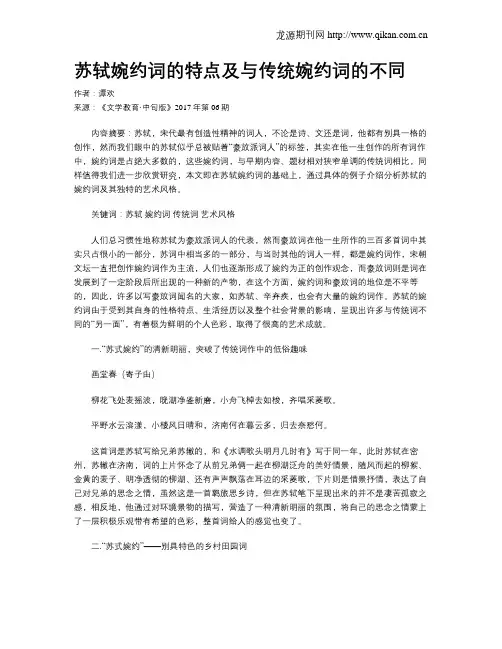
苏轼婉约词的特点及与传统婉约词的不同作者:谭欢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7年第06期内容摘要:苏轼,宋代最有创造性精神的词人,不论是诗、文还是词,他都有别具一格的创作,然而我们眼中的苏轼似乎总被贴着“豪放派词人”的标签,其实在他一生创作的所有词作中,婉约词是占绝大多数的,这些婉约词,与早期内容、题材相对狭窄单调的传统词相比,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欣赏研究,本文即在苏轼婉约词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例子介绍分析苏轼的婉约词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传统词艺术风格人们总习惯性地称苏轼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然而豪放词在他一生所作的三百多首词中其实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苏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与当时其他的词人一样,都是婉约词作,宋朝文坛一直把创作婉约词作为主流,人们也逐渐形成了婉约为正的创作观念,而豪放词则是词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一种新的产物,在这个方面,婉约词和豪放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许多以写豪放词闻名的大家,如苏轼、辛弃疾,也会有大量的婉约词作。
苏轼的婉约词由于受到其自身的性格特点、生活经历以及整个社会背景的影响,呈现出许多与传统词不同的“另一面”,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苏式婉约”的清新明丽,突破了传统词作中的低俗趣味画堂春(寄子由)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
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
这首词是苏轼写给兄弟苏辙的,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同一年,此时苏轼在密州,苏辙在济南,词的上片怀念了从前兄弟俩一起在柳湖泛舟的美好情景,随风而起的柳絮、金黄的麦子、明净透彻的柳湖、还有声声飘荡在耳边的采菱歌,下片则是借景抒情,表达了自己对兄弟的思念之情,虽然这是一首羁旅思乡诗,但在苏轼笔下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凄苦孤寂之感,相反地,他通过对环境景物的描写,营造了一种清新明丽的氛围,将自己的思念之情蒙上了一层积极乐观带有希望的色彩,整首词给人的感觉也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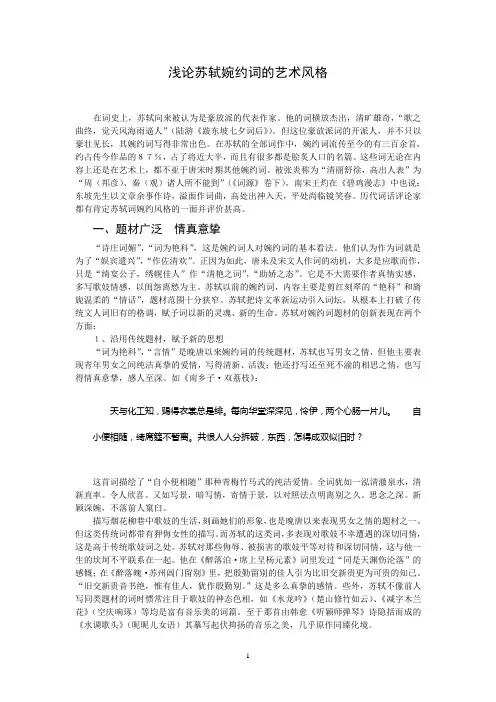
浅论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在词史上,苏轼向来被认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
他的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
但这位豪放派词的开派人,并不只以豪壮见长,其婉约词写得非常出色。
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流传至今的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87%,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被张炎称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词源》卷下)。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面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
历代词话评论家都有肯定苏轼词婉约风格的一面并评价甚高。
一、题材广泛情真意挚“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这是婉约词人对婉约词的基本看法。
他们认为作为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作佐清欢”。
正因为如此,唐未及宋文人作词的动机,大多是应歌而作,只是“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作“清艳之词”,“助娇之态”。
它是不大需要作者真情实感,多写歌妓情感,以闺怨离愁为主。
苏轼以前的婉约词,内容主要是剪红刻翠的“艳科”和旖旎温柔的“情话”,题材范围十分狭窄。
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引入词坛,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人词旧有的格调,赋予词以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苏轼对婉约词题材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1、沿用传统题材,赋予新的思想“词为艳科”,“言情”是晚唐以来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苏轼也写男女之情,但他主要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得清新、活泼;他还抒写还至死不渝的相思之情,也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如《南乡子·双荔枝》: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
每向华堂深深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筵不暂离。
共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这首词描绘了“自小便相随”那种青梅竹马式的纯洁爱情。
全词犹如一泓清澈泉水,清新直率。
令人欣喜。
又如写景,暗写情,寄情于景,以对照法点明离别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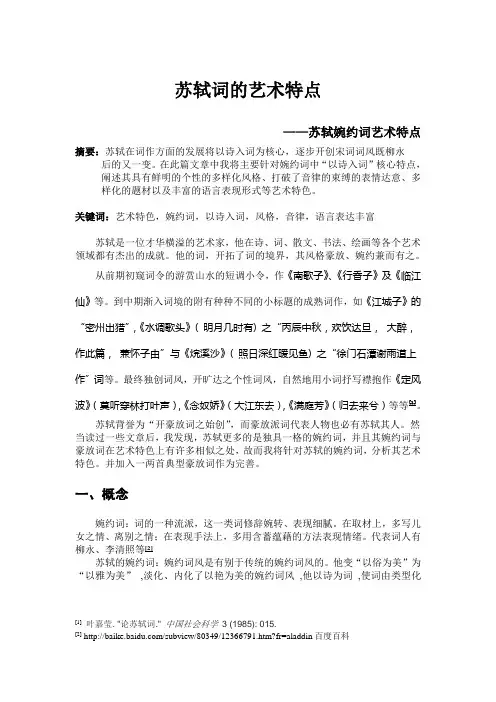
苏轼词的艺术特点——苏轼婉约词艺术特点摘要:苏轼在词作方面的发展将以诗入词为核心,逐步开创宋词词风既柳永后的又一变。
在此篇文章中我将主要针对婉约词中“以诗入词”核心特点,阐述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多样化风格、打破了音律的束缚的表情达意、多样化的题材以及丰富的语言表现形式等艺术特色。
关键词:艺术特色,婉约词,以诗入词,风格,音律,语言表达丰富苏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的词,开拓了词的境界,其风格豪放、婉约兼而有之。
从前期初窥词令的游赏山水的短调小令,作《南歌子》、《行香子》及《临江仙》等。
到中期渐入词境的附有种种不同的小标题的成熟词作,如《江城子》的“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与《烷溪沙》( 照日深红暖见鱼) 之“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词等。
最终独创词风,开旷达之个性词风,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满庭芳》(归去来兮)等等[1]。
苏轼背誉为“开豪放词之始创”,而豪放派词代表人物也必有苏轼其人。
然当读过一些文章后,我发现,苏轼更多的是独具一格的婉约词,并且其婉约词与豪放词在艺术特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故而我将针对苏轼的婉约词,分析其艺术特色。
并加入一两首典型豪放词作为完善。
一、概念婉约词:词的一种流派,这一类词修辞婉转、表现细腻。
在取材上,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情;在表现手法上,多用含蓄蕴藉的方法表现情绪。
代表词人有柳永、李清照等[2]苏轼的婉约词:婉约词风是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风的。
他变“以俗为美”为“以雅为美”,淡化、内化了以艳为美的婉约词风,他以诗为词,使词由类型化到个性化,给传统婉约词注入了活力和生气。
本文试就苏轼对婉约词风由俗而雅,对以艳为美的婉约词风的淡化、内化及词的个性化等方面谈一些浅见。
[3] 现存东坡词三百余首于《东坡乐府》中, 词风不拘一格, 现根据其三个发展阶段,试举他的几首婉约词加以赏析, 以探索苏轼这一类词之的艺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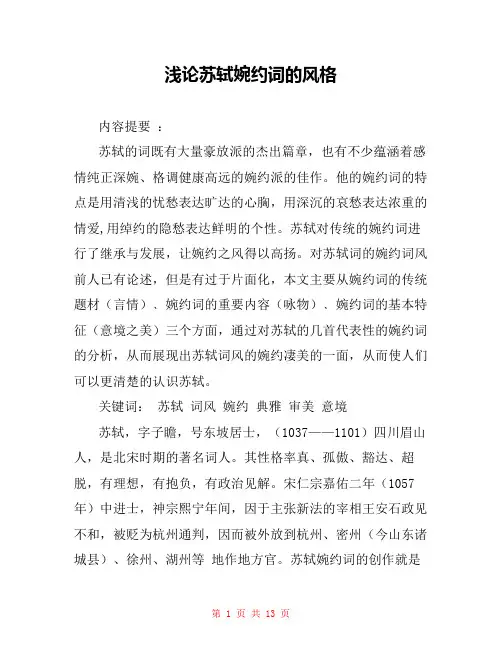
浅论苏轼婉约词的风格内容提要:苏轼的词既有大量豪放派的杰出篇章,也有不少蕴涵着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的婉约派的佳作。
他的婉约词的特点是用清浅的忧愁表达旷达的心胸,用深沉的哀愁表达浓重的情爱,用绰约的隐愁表达鲜明的个性。
苏轼对传统的婉约词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让婉约之风得以高扬。
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苏轼词风婉约典雅审美意境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
其性格率真、孤傲、豁达、超脱,有理想,有抱负,有政治见解。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因而被外放到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湖州等地作地方官。
苏轼婉约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后被新党中部分人罗织文字狱,兴起“乌台诗案”,下狱史狱,经救援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
旧党执政后,被招还,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但又与旧党意见分歧,遭排挤出任杭州、颖州等地地方官。
当变了质的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儋县)等地,徽宗即位时遇赦北还,死于常州。
苏轼,其婉约词具有很高的成就。
他作婉约词有其感情基础、历史原因、才力因素.其词塑造了亡妻、舞妓、少女等形象,借词抒发其政治情怀;铺叙、比兴等是其常用表现手法,结构方式灵活多样;其语言极为洗炼、凝重,常选用一些凄冷哀婉之词,点化作者心境.总之,其婉约词塑造形象的成功、抒发感情的真切、表现手法的纯熟、运用语言的巧妙,使其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豪放词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婉约词人。
苏轼现存词作中,婉约词数量远远多于豪放词,这些委婉含蓄之作,无论是抒发亲人,恋人间的深厚情谊,还是表现士大夫之流的闲情逸致,无论是对田园风格的尽情讴歌,还是对寄情之物的着力咏叹,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滋润着词人特有的审美意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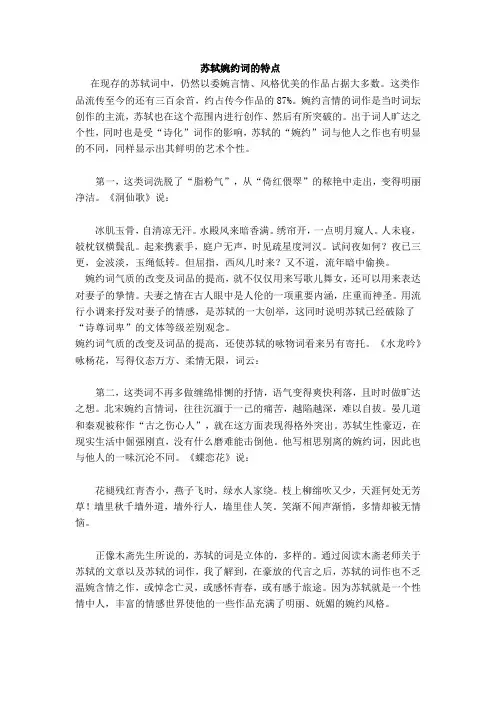
苏轼婉约词的特点在现存的苏轼词中,仍然以委婉言情、风格优美的作品占据大多数。
这类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87%。
婉约言情的词作是当时词坛创作的主流,苏轼也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创作、然后有所突破的。
出于词人旷达之个性,同时也是受“诗化”词作的影响,苏轼的“婉约”词与他人之作也有明显的不同,同样显示出其鲜明的艺术个性。
第一,这类词洗脱了“脂粉气”,从“倚红偎翠”的秾艳中走出,变得明丽净洁。
《洞仙歌》说: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敧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婉约词气质的改变及词品的提高,就不仅仅用来写歌儿舞女,还可以用来表达对妻子的挚情。
夫妻之情在古人眼中是人伦的一项重要内涵,庄重而神圣。
用流行小调来抒发对妻子的情感,是苏轼的一大创举,这同时说明苏轼已经破除了“诗尊词卑”的文体等级差别观念。
婉约词气质的改变及词品的提高,还使苏轼的咏物词看来另有寄托。
《水龙吟》咏杨花,写得仪态万方、柔情无限,词云:第二,这类词不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得爽快利落,且时时做旷达之想。
北宋婉约言情词,往往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晏几道和秦观被称作“古之伤心人”,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
苏轼生性豪迈,在现实生活中倔强刚直,没有什么磨难能击倒他。
他写相思别离的婉约词,因此也与他人的一味沉沦不同。
《蝶恋花》说: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正像木斋先生所说的,苏轼的词是立体的,多样的。
通过阅读木斋老师关于苏轼的文章以及苏轼的词作,我了解到,在豪放的代言之后,苏轼的词作也不乏温婉含情之作,或悼念亡灵,或感怀青春,或有感于旅途。
因为苏轼就是一个性情中人,丰富的情感世界使他的一些作品充满了明丽、妩媚的婉约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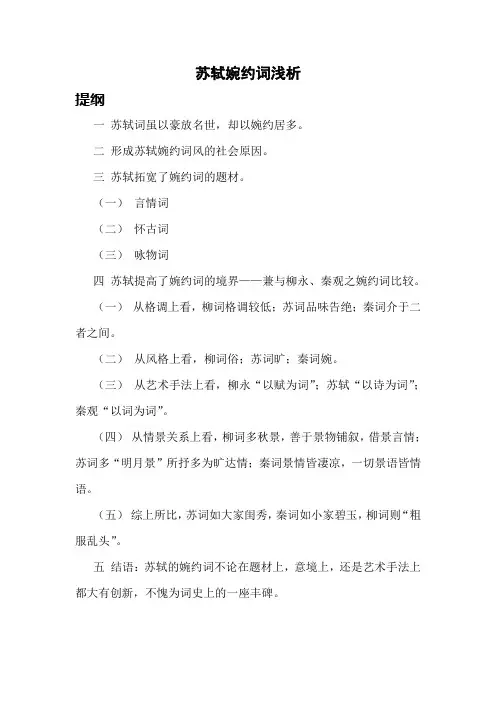
苏轼婉约词浅析提纲一苏轼词虽以豪放名世,却以婉约居多。
二形成苏轼婉约词风的社会原因。
三苏轼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
(一)言情词(二)怀古词(三)咏物词四苏轼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兼与柳永、秦观之婉约词比较。
(一)从格调上看,柳词格调较低;苏词品味告绝;秦词介于二者之间。
(二)从风格上看,柳词俗;苏词旷;秦词婉。
(三)从艺术手法上看,柳永“以赋为词”;苏轼“以诗为词”;秦观“以词为词”。
(四)从情景关系上看,柳词多秋景,善于景物铺叙,借景言情;苏词多“明月景”所抒多为旷达情;秦词景情皆凄凉,一切景语皆情语。
(五)综上所比,苏词如大家闺秀,秦词如小家碧玉,柳词则“粗服乱头”。
五结语:苏轼的婉约词不论在题材上,意境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大有创新,不愧为词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苏轼词虽以豪放名世,却以婉约居多在一般的文学史教材中,苏轼都是以豪放派的开山之祖出现的。
的确,苏轼的“三百多首《东坡乐府》一向被公认为词坛上的一座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一个新的流派的开创者;再词的发展史上,他更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
”(沈祖棻《宋词赏析》)“从绝对数量上讲,苏祠还是以婉约之作为最多,这对于一个风格多样的大作家本不足怪,更何况苏轼是生活在婉约为宗的时代。
”(赵仁珪《论宋六家词》)王水照先生也说:“他所写的传统的爱情题材的创作,仍以婉约见长。
他吸取了婉约派词人抒情的真挚和细腻,又显示出深沉、醇厚的自家面目。
”(《苏轼》)吴世昌先生说的更是直截了当:“苏轼的所谓豪放词,如‘大江东去’、之类,在他全部词作中至多只有十来首,仅为全集的百分之三。
旖旎风光的词占绝大多数。
”“东坡有哪些‘豪放词’于是翻开每一本文学史或词论,照例举出了‘大江东去’、‘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等几首……”“《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手都要称赞歌女舞伎(“佳人”),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
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简析_苏轼的诗词代表作有哪些苏轼是北宋文坛革新的杰出领袖,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全能的文学天才。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那么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是怎样的?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希望对你有用!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一、气势恢弘、激情磅礴的豪放风格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是豪放词的代表,他能够借助瑰丽恢宏的意象来抒发慷慨豪情,将充沛激昂或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并开拓了词的写作范围。
(一)气势磅礴、场景宏阔雄壮气势恢弘。
苏词的豪放词有气势豪迈飞动、场景宏阔雄壮的特点。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一首著名的豪放词,磅礴的气势、壮美的场景、雄浑的境界,正是豪放词风的体现。
词的上片写景,描写赤壁的景色,前三句,仿佛是描述远景,长江水浩浩荡荡,滔天波浪如大浪淘沙,送走了一代风流人物;次三句,描写近景,目光投向赤壁古战场;上片最后两句,是上片景物描写的总结。
下片怀古,词人抓住周瑜年轻有为的主要特征,塑造了他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并由此联想到自己华发早生,功业无成,不免产生人生如梦之感。
总体来看,这首词从江水的东流,感受到时光的逝去,进而把江山与人物合写,使“江山如画”与“风流人物”都得到形象的表现,写得雄浑豪放,气象恢弘,堪称历代咏史怀古诗词之绝唱,亦开后世豪放一派之先河,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这类词还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诠》(落日绣帘卷)等。
(二)直抒胸臆,自由豪放豪情奔放。
苏轼的词注重抒情言志,直抒胸臆,自由豪放。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诗词鉴赏苏轼的豪放与婉约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宋代文坛的领袖之一。
他的诗词作品以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而闻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表达能力。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苏轼的豪放与婉约之美。
一、苏轼的豪放苏轼的豪放风格表现在他的豪放情怀和自由奔放的写作风格中。
在《赤壁赋》中,苏轼以雄辩慷慨的笔触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和激荡人心的历史场景,展现出他的豪情壮志。
他经常运用雄浑激越的辞藻和瑰丽而奔放的叙述手法,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所蕴含的壮志豪情。
苏轼的豪放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坦荡看法和不拘一格的个性上。
他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嘲地形容自己的性格。
他不受世俗规则束缚,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这种坦率直接的性格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苏轼的婉约苏轼的婉约之美主要体现在他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委婉细致的写作风格中。
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细腻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他深情地表达了对亲人、朋友和故土的眷恋,同时也在悲欢离合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深情。
苏轼的婉约还体现在他对自然的细腻观察和精心描绘上。
他能以朴实的言辞揭示出自然界中微妙的变化和神秘的力量,如《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句,以简洁的文字表达出对月亮和人生的深思。
三、豪放与婉约的结合苏轼的诗词作品中也有一些既有豪放的气势,又有婉约的柔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豪放与婉约的特点完美结合。
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这首词中既豪放地描绘了战争的场面,又婉约地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使整首词既有慷慨激昂的气势,又有温柔细腻的情感。
在苏轼的豪放与婉约之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真理的追求。
他的作品既展现了豪情激荡的壮丽景象,又体现了内敛婉约的情感体验,这种综合的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独具一格,赋予了读者丰富的审美享受。
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的婉约词风1. 引言1.1 概述苏轼,北宋时期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学家,他的诗词作品以婉约清丽脱俗而闻名于世。
其中,《水调歌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古代词中的瑰宝。
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苏轼《水调歌头》中所体现的婉约词风,并探讨其在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首先,我们将介绍苏轼和婉约词风的背景知识,帮助读者对相关内容有更全面的了解;接着,我们将详细剖析《水调歌头》具有温柔细腻的笔触、纤巧婉转的表达方式以及对情感和人生的独特见解等婉约词风特点;然后,我们将通过具体分析《水调歌头》中描写自然景色与人物形象、表达对时代和社会境况、抒发对爱情和人性理解等方面来展现其中蕴含的婉约之美;最后,在结论部分概括苏轼《水调歌头》中的婉约词风特点,分析其在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和价值。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深入探讨苏轼《水调歌头》中所体现的婉约词风,通过对其温柔细腻的笔触、纤巧婉转的表达方式以及对情感和人生的独特见解等方面进行分析,展示其在描写自然景色与人物形象、表达对时代和社会境况、抒发对爱情和人性理解等方面的婉约之美。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苏轼在古典文学史上的贡献,并从中获得对当代诗歌创作及审美追求的启示。
2. 背景介绍:2.1 苏轼简介: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杰出人物之一,被誉为“文房四宝”之首。
苏轼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从小就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艺术天赋。
他不仅擅长诗词创作,还善于书法,并且在文学批评、历史评论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苏轼一生经历了多次官场变故,曾被贬谪多次,但无论身处何地,他都保持着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和热爱。
2.2 婉约词风概述:婉约词风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诗词时常使用的一种风格。
婉约词风追求温柔、细腻、柔美、含蓄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缠绵唱和、委婉含蓄的艺术效果。
论苏轼的婉约词[石占德]内容摘要:文学史上婉约词的词作传统对苏轼的影响使其创作了大量的婉约词,但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对婉约词进行了重大的突破与革新,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因此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婉约词:一苏轼写婉约词有其历史必然性。
我用以下四个观点为论据来证明:首先,纵观词的发展,从词的产生到北宋中期,基本上仍是婉约词一统天下。
其次,从词本身来看,词最初并不是专供观览的案头文学,而是配合新兴乐曲演唱的歌词,所以词又有曲、曲子、曲子词之称。
其三,从苏轼的经历和思想来看,他也有写作婉约词的情感基础。
其四,就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来说,它们并不是水火不容相互排斥的。
二苏轼对婉约词的革新。
(一)开拓了婉约词的题材、内容。
1、描写农村题材的词。
用[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为论据。
2、悼亡词。
用《江城子》《西江月》两首词的内容、意境、构思分析,毛泽东的悼亡词与苏轼悼亡词比较为依据。
3 、咏物词中的柔美情怀,苏轼的咏物词使婉约词的气质和词品得到了提升。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为论据。
4、苏轼词诉说了真挚的亲朋情感。
以《沁园春》苏轼赴密州任旅途中寄子由的分析为据。
5 、苏轼词展现了清新秀丽的水色山光。
《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
”为论据。
6、苏轼闺阁词中的少女情怀7、苏轼婉约词中的思乡情怀。
例如:[醉落魄]离京口作(二)苏轼婉约词追求“以雅为美”。
1、他的词婉约词洗脱了“脂粉气”,变得明丽净洁。
以[洞仙歌]为例“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说明。
2 、用语文雅也是苏轼婉约词刻意追求的。
对[永遇乐]《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首词的分析为论据。
(三)苏轼的“婉约词”与他人之作也有明显的不同,同样显示出其鲜明的个性。
第一:同样是写“婉约词”他突破了糜烂生活的低俗气味,词中流露出一种清新明丽之情。
第二:他的婉约词不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的爽快利落,且时时做旷达之想。
论苏轼的婉约词王艳芳内容摘要:苏轼一直因为他的豪放词而为人熟知,但是他的婉约词也占了更大的一部分,而且也有很高的成就。
本文从苏轼婉约词的成因、内容题材和艺术创新等方面来对苏轼的婉约词进行讨论,并论述苏轼婉约词的贡献。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艺术创新;贡献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词、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杰出的成就。
一般我们都把他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他们被看成是豪放派词的主要代表人物。
有学者引用北宋胡寅的一段话来形容苏轼对词体革新的特殊贡献:“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①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确是豪放词的创立者,但是他的婉约词也有极高的成就。
苏轼作诗在前,他流传下来的诗远较词多,有2700多首诗,他的词只有300多首。
但是苏轼对词的发展有极大贡献,他创立了豪放词,革新了婉约词。
他以诗为词,扩大了诗的题材,以词的形式记游咏物,怀古伤今,歌颂祖国的壮丽山川,抒发个人的豪情与伤感,他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
虽然一般都把苏轼当成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在现存的三百多首苏词中,绝大数仍属婉约词。
因此在苏词研究中,他的婉约词是不可忽视的。
词自从产生以后, 特别是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手里, 一直以婉约为正宗, 多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 尤侧重儿女风情。
豪放派词人中,不管是苏轼还是辛弃疾都有不少婉约词问世,甚至在一首词中都会体现出刚柔相济的一面。
苏轼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其实是位能豪能婉、亦刚亦柔的词人,我们不能忽视苏轼的婉约词。
本文将分别对苏轼婉约词的成因、苏轼婉约词的内容和艺术特点以及苏轼婉约词的贡献展开探讨。
一、苏轼婉约词的成因苏轼成为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这是由他的时代、生活经历、生存环境、思想性格、文化素养等各种因素造就的。
毫无疑问,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其婉约词的成因,也与这些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将苏轼婉约词的词风的成因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词的发展来看,婉约词一直被奉为正宗,苏东坡不可能摆脱其影响。
浅析苏轼婉约词的特色“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初识苏轼,正是从这几句词开始的。
词的意境在月的阴晴圆缺中,处处透着浓厚的哲学意味,虚实相织,让人仿佛置身梦境。
在中国文化史上,唐诗宋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特别是侧重儿女风情、离别之情的婉约词,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更是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一、苏轼与婉约词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州眉山(今四川)人。
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合称“三苏”。
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
卒后追谥文忠。
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
留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
一提起苏轼,人们总会想起他是豪放派词的开山鼻祖。
但纵观苏轼词,豪放辞章并没有占多数,更多的还是婉约含蓄的篇目。
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多言情,往往以美取胜。
在现存的三百余首东坡词中,堪称豪放词的不过三四十首,仅占十分之一左右,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妩媚的婉约词。
苏词的风格除豪放旷达之外,或呈隽永质朴的风姿,或具明快秀丽的神韵。
可以说苏轼的确是一位能豪能婉、能刚能柔的词坛多面手。
他不仅开创了豪放一派,婉约词也写的韵味深厚,有的还能熔豪放、婉约为一炉,是婉约词独具个人风采。
二、苏轼婉约词的特色的具体表现苏轼的婉约词,或多或少地透出一种“愁”绪,只是不是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一种隐隐约约、若隐若现的感觉,一种故意隐藏的感觉:1、旷达的心胸中透着清浅的忧愁在苏轼的婉约词中,他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而是语气爽快利落,做旷达之想,常把很多诗人笔下悱恻的哀愁轻描淡写,这是苏轼婉约词的一大特色。
他写相思别离的婉约词,就与他人的一味沉沦不同,比如他在《蝶恋花》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首词作于“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暮春季节,这本来是一个“枝上柳绵吹又少”之花落花飞令人伤感的季节,如果作者的心境不佳,就更容易被凄苦悲愁的情绪所缠绕。
浅论轼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在词史上,轼向来被认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
他的词横放杰出,清旷雄奇,“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
但这位豪放派词的开派人,并不只以豪壮见长,其婉约词写得非常出色。
在轼的全部词作中,婉约词流传至今的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87%,占了将近大半,而且有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些词无论在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不亚于唐宋时期其他婉约词。
被炎称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观)诸人所不能到”(《词源》卷下)。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面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
历代词话评论家都有肯定轼词婉约风格的一面并评价甚高。
一、题材广泛情真意挚“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这是婉约词人对婉约词的基本看法。
他们认为作为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作佐清欢”。
正因为如此,唐未及宋文人作词的动机,大多是应歌而作,只是“绮宴公子,绣幌佳人”作“清艳之词”,“助娇之态”。
它是不大需要作者真情实感,多写歌妓情感,以闺怨离愁为主。
轼以前的婉约词,容主要是剪红刻翠的“艳科”和旖旎温柔的“情话”,题材围十分狭窄。
轼把诗文革新运动引入词坛,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文人词旧有的格调,赋予词以新的灵魂、新的生命。
轼对婉约词题材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1、沿用传统题材,赋予新的思想“词为艳科”,“言情”是晚唐以来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轼也写男女之情,但他主要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写得清新、活泼;他还抒写还至死不渝的相思之情,也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如《南乡子·双荔枝》: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
每向华堂深深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筵不暂离。
共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这首词描绘了“自小便相随”那种青梅竹马式的纯洁爱情。
全词犹如一泓清澈泉水,清新直率。
令人欣喜。
又如写景,暗写情,寄情于景,以对照法点明离别之久。
思念之深。
新颖深婉,不落前人窠臼。
描写烟花柳巷中歌妓的生活,刻画她们的形象,也是晚唐以来表现男女之情的题材之一。
但这类传统词都带有狎侮女性的描写。
而轼的这类词,多表现对歌妓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这是高于传统歌妓词之处。
轼对那些侮辱、被损害的歌妓平等对待和深切同情,这与他一生的坎坷不平联系在一起。
他在《醉落泊·席上呈元素》词里发过“同是天渊伤沦落”的感慨;在《醉落魄·阊门留别》里,把殷勤留别的佳人引为比旧交新贵更为可贵的知已。
“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些外,轼不像前人写同类题材的词时惯常注目于歌妓的神态色相,如《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减字木兰花》(空庆响琢)等均是富有音乐美的词篇。
至于那首由愈《听颖师弹琴》诗隐括而成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其摹写起伏抑扬的音乐之美,几乎原作同臻化境。
伤怀别人也是婉约词传统题材。
在晚唐伤怀别人词中,对象主要是女性,容为恋情。
轼在创作此类词时,不但表现男女之间的离愁别苦,还扩大到送别挚友、怀念亲人的围。
如〈昭君怨·送别〉,写作者与友人的恋恋不舍,依依惜别,表达出缠绵的别情。
又如《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一首情念亡故的恩师欧阳修的词。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作者把自己与明月都看成“识翁人”。
实以明月自比,表示对欧阳修情谊的永恒和纯洁。
轼与兄弟辙的友爱,那是著名的,手足之情,使他对兄弟异常怀念。
如在《西江月·中秋》中说:“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满江红·怀子由作》中说:“辜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
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
这与传统伤怀别人题材相比,增加了较多的社会容。
2、开拓婉约词新的题材领域首先,轼将咏物之作引入词中。
托物言志本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晚唐五代词中却绝少咏物词。
高水平的咏物词当是:借物言情,以物达志。
达到物中有我,我中有物,咏物与寓意的高度融合。
欲达此境界,则香草美人的婉约笔法最为适宜。
轼婉约词中的咏物之作并不很多,却达到了咏物词的极致,吟咏围也很广泛。
在他笔下,有凌霜傲雪,催人奋发的青松;有令人赏心悦目,梦回酒醒的白芙蓉;有“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梅花;有“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的荔枝;甚至还有“斗赢一水,功敌千盅,觉凉生两腋清风”的清茶……通过咏题,轼含蓄地将自己的品格、理想和情趣溶入了松梅等物的精神之中,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咏物极境。
例如《卜算子·写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写于。
当时轼因“乌台诗案”遭贬,只身寄寓于凄凉的定惠院。
因刚刚出狱,惊魂未定,又“郡中无一识者”,故常策杖江边,望云而茫然,心境孤寂苦闷。
这种幽独孤愤之思,在其时写的诗中多有表现。
如《海棠》诗云:“只有名花苦幽独”;《月夜偶出》云:“清诗独吟还自和”等。
上述这首词则是轼于深夜难眠、月下独步之际,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情与物会,遂将满腹幽愤,借孤鸿形象和盘托出。
孤鸿惊起却频自回首者,乃抒发了诗人猝遭迫害,一腔怨恨无可倾诉之孤愤。
而拣尽寒枝却终宿沙洲者,正表现了他虽处穷厄却不屈身随人的孤高自守的情操。
词以拟人化手法写得语近意远,含而不露,很切合轼当时的心境。
王安石变法前,轼亦主变革的。
王安石变法后,在变法容与方法上,他与王安石不和,又更多地看到新法的弊端,而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因而遭到贬斥。
在外放期间,轼勤于政务,也确实看到新法于民不利的一面,遂作诗托事以讽,本是希望君主能察知民隐,“庶几有补于国”,竟被诬陷这“诽谤时政”而下狱、远贬。
后来,轼回首这些往事时说,如果他当时稍加俯就,凭他的地位和名望,是可以得到重用,甚至飞黄腾达的。
但他却自甘幽独,誓为苟合。
这不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静沙洲冷”最好的注脚吗?再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因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花,点点是离人泪。
“轻薄花逐水流”本是腐的题目,但到了轼手里却翻也了新意。
在这首和词里,他借花的“抛家傍路”抒发了自已贬谪的飘泊之感。
花漫天飞舞,纷纷飘坠,竟无人怜惜,忍看酿就春色、装点春光的美好事物凋零、陨落。
字里行间正寄寓了词人那种万感丛集、中无主的深广忧愤。
“抛家傍路”既是花真实写照,也映现着作者才难为用、一任飘泊的迁客逐臣的现实处境。
全词以迷离惝恍之笔,写郁塞彷徨之感,既抓住了花之神,又摄取了人的魂魄力。
由人体物,心与物游;借物写人,神与人合,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难辨的境界。
诚如谦所说:“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
”王国维也对之推崇备至:“咏物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1)。
其次,在词中描写农村风光,轼可称第一人。
描绘田园景色和农村风光,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题材,而在轼的词作中,农村题材的词作约占全部词的十分之一。
可见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关注。
他写农村的词作风格多样,其中一部分写得清丽妩媚,词情宛转,当属婉约词之列。
最为有名的是他在任上所作的五首《浣溪沙》。
这是为了城东石潭雨而作。
轼以清新明丽之笔,写出了农村的秀丽风光,讴歌农民繁忙的劳作和雨后喜悦的心情。
在词人笔下,有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者等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有春末夏初,麦收在望的农村风光;还有缫丝、赛神、观使君等农村风情。
词中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
读来象风物画那样令人神往,也如抒情乐曲般沁人肺腑。
词中含蓄、蕴藉之处,颇能诱发读者的遐思与想象。
其四云: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在一般文人眼里,枣花既无丽色,又无馨香,且屑细如粉,难入诗词。
但在轼笔下却颇有生气,落在衣巾上竟能簌簌有声!这正反映了轼对农村风光的热爱和普降喜雨后的怡悦心情。
结尾也很发人深思:“野人”尚能赐我一杯粗茶,解我之渴,而我“使君”当赐农何家?贬官后,轼又写了五首吟咏农村风光的《浣溪沙》。
但时过境迁,词的情调不复从前那样欢悦。
如“翠袖倚风萦柳絮,降唇得酒烂樱珠。
樽前呵手镊霜须。
”虽然似“哀高丘之无女”的情调,不失轼的风流儒雅,但实际上是恢谐其外,寓凄苦。
这种游戏谑浪之语,虽符合传统的婉约词风格,反映的却是轼对农民疾苦的关怀:“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此种题材,此等胸襟,轼之前的婉约词中是没有的。
二、意境清新格调高雅北宋词坛盛行婉约词,轼的婉约词多数也是袭用传统的题材。
诸如男女之情、羁族伤怀别、饮宴酬赠等等,但他写得清丽流畅,情趣高雅,大大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
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爱情词,多写男欢女悦,幽会密约,其词情浮艳,充满脂粉气“。
擅长写都市风光与农民生活的柳永,虽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但其艳情词亦往往寄情声色,醉于依红偎翠,故情趣不高。
轼却与之不同,他的爱情词体现了“天工与清新”的格调,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爱恋的纯真和伉丽的情深意笃,以至生死不渝。
仅以被王士祯称赞连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为例,抛开词人以香草、美人手法寄寓自己的政治失意不说,只看那“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儿女情,它也是健康、纯洁,充满活力的。
轼十分珍重夫妻之情,为后世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爱情诗篇——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这首被誉为“心思之曲”的词中,轼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典型性的事物和迷离恍惚的梦境描写,抒写了对亡妻王弗的刻骨怀念,表达对亡妻生死不渝的爱情。
封建时代的文人向有写悼亡作品的传统,其中岳的《悼亡诗》和元稹的《遣悲戚》都是古今传诵的佳作,和这两首诗比较,轼的悼亡词,既不像岳那样单纯写追忆当年鸳鸯的双飞双栖生活,也非元稹那样写富贵显达后对亡妻的追念,而是写仕途坎坷、政治怀抱难以施展时,对曾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体贴他的贤德亡妻的怀念。
这种久郁于胸的哀愤之情,通过梦境潮水般宣泄出来。
比之岳、元稹之一诗,感情更为真挚,忧愤尤为深广,遂成千古绝唱。
这首词之所以有如此震憾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怀人”成分。
亲人的死亡对生者来说是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和摧伤,因为死者不能复生,绝了生者与之再见之望。
但轼却顽固地不肯绝此再见之望,亡妻在他心里依然是十年前活灵活现的娇妻。
他是以“怀人”的心思来写悼亡的,总企盼有一天能与妻子相聚,向他诉说这几年的凄凉。